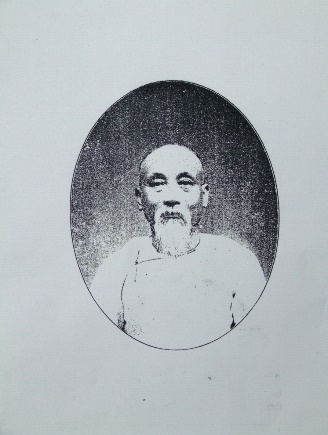从“李公塘”到“人民塘”
李超琼,字紫璈,四川合江人,放牛娃出身的拔贡,青年时代在辽东做过多年军务幕僚。经过多次乡试,三十二岁才中举为官,先后在江南的溧阳、元和、阳湖、江阴、无锡、吴县任县令。他顾怜百姓,不阿长吏,不欺细民,每临一县,倾全力兴筑惠民工程,救百姓于水火;他不惜财政亏累,多次领头向上争取,为地方申报蠲免税赋;他洁身自好,处膏不润。他曾四次获得朝廷的“卓异”嘉奖,但到东到西,做来做去,一直只是个大清皇朝最基层的芝麻官——县令。光绪三十一年(1905)调任南汇县令时,他已经五十八岁了。
修补海塘为当时南汇县的第一要务。筑塘,最要紧是银子。他是个穷县令,县库却空空如也。每逢灾荒,他只能出头多方筹集赈灾钱粮,向上争取“截漕”济民,争取蠲免或部分蠲免百姓当年赋税。知县李超琼的“一人财政”,长年处于入不敷出、严重亏损中。
李超琼在取得了两万九千两积谷银借款之后,又从藩库借到了截漕银一万两。
浦东南汇新海塘筑成后,它相对王公塘而被叫做“新塘”。“李公塘”,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在书面文献中,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的《南汇县续志》。从来没有人题字勒碑,口口相传,自然而然而已。这就是口碑。

1949年8月,上海市长陈毅将军亲临浦东海塘决口指挥抢修加固(图片由上海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1949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晚,当年的六号台风正面袭击南汇的祝桥、老港。那天强风、暴雨,又恰好与天文高潮相遇,潮位高达五点一八米,李公塘又被冲决。海塘之内,汪洋一片。上海市长陈毅亲临海塘决口,冒雨指挥抢修加固。灾后,经陈毅提议,重生的李公塘改名为“人民塘”。
自治选举和生命尽头
宣统元年(1909)元月,朝廷有谕旨下达:“本年各省均应举行咨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闰二月,江苏省咨议局选举开始,上海县令李超琼担任上海县选区的初选监督。
初一一大早,他就乘着马车,冒着雨,开始对辖区内的十个选区逐个巡视。最先去了火神庙一带的第一选区。关帝庙一带是第二选区。西门外官契局一带是第四选区,返回县城,再出东门,商务分局一带是第三选区,看到选民“来者亦盛”。天后宫内的第五选区,情况也很不错。
初四是初选投票日。投票之箱,是事先封锁的。李超琼是初选监督,选票是否有效,都由他审决。投票场所,各种角色分职任事,形容整肃,井然有序。上海县衙里的丞、簿、尉等吏员也被调来帮忙。
这次选举,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选举范围太小,代表性远远不够,但其意义非同小可。中国人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后,用选票选出参与公共事务的代表,毕竟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十一日,是李超琼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孙侍郎由京来沪,他去侍郎下榻的汇中西旅馆拜谒。上海道的蔡道台也在。下午,李超琼来到日晖港参加一条新建马路的通车礼。晚餐后,李超琼像往常一样,处理案牍至时钟敲过十点。然后写日记,这是他数十年未尝或辍的事情。
他回到自己的寝室,又与外甥徐子莪说了一会儿话。徐甥是二姐静恒的儿子,二姐夫去世后,一直在他的衙门里帮做收发。每天都一样,直到他脱衣就寝,徐甥才掩门出去。半夜里,忽然他房里传出叫人的铃声,待二儿子廷昂闻声赶到,常年积劳成疾的李超琼已经足伸目暝,与世长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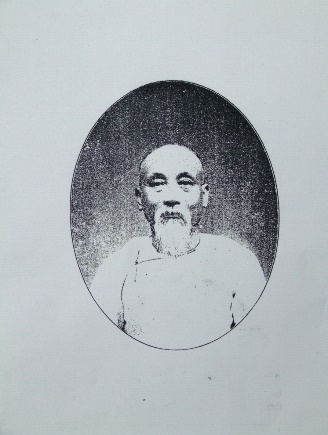
李超琼晚年肖像(图片由苏州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提供)
李超琼有四个儿子,老三早夭。此时,长子廷毅远在合江老家务农,老四廷侃在日本留学。老二廷昂正好来上海探亲,于是便成了父亲临终在场的唯一的儿子。
“处膏不润”,“其卒几无以为殓”
上海县令李超琼逝世的消息,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申报》称:“正任李县令身后萧条,(债务)积累颇重,殊觉惨然。”事实上,家里已经不名一钱,连丧葬费用都凑不出,“几无以为殓”
上海士绅行动起来,先由总工程局牵头,筹集白银一千两为李超琼治丧。然后,上海士绅在《新闻报》联名发表《上海士绅上督、抚电:为李故令乞恩免追亏欠》,向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请求破例免于追缴李超琼的亏欠。还公布了《故令亏欠细账》,说明李超琼的亏欠,都只是因公亏欠。
清朝廷对漕项拖欠的追讨向来严厉。即便是因公亏空,也要求地方主官负责弥补,不惜革职查办,变卖家产,哪怕人死了也要追讨到底。时任江苏巡抚的瑞澂对上海士绅们的联名请求的回应十分明确:“不能允准”。瑞澂做事,代表朝廷的意志,“公事公办”。
士绅领袖李平书是上海滩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月后的三月初十,他以上海士绅的名义,在小西门白云观为李超琼举办追悼大会,有市民一千多人参加。他亲自登台,向市民和报界公开李超琼“因公亏累细数”, 并且提出“筹备弥补之策”。
李平书讲话说,已故县令李超琼“于吴县任内亏银三万四千余两,南汇任内亏银四万一千余两,上海任内亏银五万五千余两,共银十三万两。”“丁、漕两项赔累”的直接原因是“钱价日跌,米价奇贵”。一切“有账可查”,“并非他项浪费”。他强烈呼吁督、抚衙门同意上报户部奏销。同时也建议,“应解之款,先行设法筹措解缴”。李超琼在吴县、南汇、上海欠缴的银两,其实与曾经任职的无锡等县,也有些连带因果关系,他建议,由无锡县士绅负责具体落实无锡等县的应解之款。
追悼会当天,李超琼曾任过知县的元和、吴县、溧阳、阳湖等八个县的士绅代表,也都应邀赶到上海小西门参加了追悼大会。他们纷纷要求重新拟定请求免追亏欠的呈文,以便列上自己的职衔和姓名,表达出他们相同的意愿。追悼大会变成了与巡抚意见唱反调的请愿大会。
晚清,辛丑条约签订后,财政入不敷出、严重亏空的州县,何止李超琼的上海县一个。“死竟无钱”的宝山县县令窦殿高便是一例;曾与李超琼共同力主冒着犯规之险,购进暹罗米百余担,平抑上海米价的南汇知县赖葆臣,也是一例。
然而,封建王朝的命数已经指日可待了,准与不准,早已不再由朝廷一方说了算了。如果把清王朝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上海、南汇、宝山诸县,松江、苏州诸府和江苏、浙江诸行省,都是大树生存仅能依赖的主要根系。这些根系蛀空烂透之日,便是大树轰然倒地之时。“落花流水春去也”,于是,所谓的李超琼亏累案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李公堤新貌
这场亏累案让人们再次认识了李超琼。八十高龄的石神杨葆光先生为李超琼编纂年谱,在年谱中并不避讳“亏累”的事实,但摆出了另一项事实:李超琼“历任二十余年,故里未增一亩之产” ;“身后不名一钱”。 辛亥光复后,李超琼的两位生前好友——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江苏都督的程德全和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江瀚,分别为他的年谱作序。程德全在年谱序中说,把李超琼的最可贵之处,概括为四个字:“处膏不润”,“息息以民心为心”,“视民如家人父子,置一身毁誉于度外”。以至于“其卒也,几无以为殓。”
一个朝廷命官,该怎样安排身后之事?李超琼早有考虑:“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理之常也,夫何作怪。”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说:“自维一介村甿,幸读书识字,遂忝窃一官,已为非分,而曾无补于君民,亦无益于家计。”而眼下,“时艰孔亟,方忧居寂处,不能效马革裹尸者以为报靖,则死又奚足惜耶?”
一旦自己“大限”,他请儿孙们记住并且照办的,有四点:一是不要请和尚、道士进门超度;二是棺材,“不得买重价者”,买二十多元钱的就足够了。后来了解了市场价格,在又一次提到身后事时,改为“在五十元之内”。三是寿衣,“可用旧有之”,缝一身绸子的裤褂,其它都用旧的衣裤。如果是冬天死,棉衣棉袍,现成就有,不必另买。切记不要多花钱。四是葬身之地,有就行,不要浪费土地。人若死在江南,就葬在江南;也可以照习俗运回四川安葬。运棺柩回川,“可将衣物、器具、书籍变卖”,充作资费。可以考虑葬在父亲墓的西边稍后丈把远的地方。不要花钱去请风水先生。
这段遗嘱的原文是:“我如不讳,勿用僧道进门。棺二十馀元者足矣。衣或缝一分䌷裤绔,馀皆用旧物。棉花衣袍褂,一一皆有。切勿多费。仍以孝衣一件穿上,我未脱服也。(本应缞麻,姑从俗耳)有地不费,即葬吴下,亦可如回川可葬大元府君墓西稍后丈许。对笔架丁峰两山间为向,即不求地师亦可。”
他还详细开列了自己的私人债务。他借着沈佺三千两银子,借汪南陔、马筱沅各一千两;借存义公商号三千两;借孙展云、吴粤生、李集甫各五百金。先前还借过李集甫三百两,都未还。曾借石怀觐、明寿经各八百银元。以上这些,都是没打欠条的“义债”,自己这辈子两手空空,无力偿还了。他寄希望于儿子们,相信哪天他们事业有成,一定记得偿还。他说,“负欠皆我之罪”。如果儿辈们“亦不能即偿”,就“只好求诸义友,缓以时日”。儿辈们应该“勉志求自立,他日有成,勿负人厚谊可也”。

李公堤上的李超琼塑像(图片由苏州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提供)
2009年,李超琼逝世一百周年,苏州市纪委、苏州工业园区工委、管委会在金鸡湖畔李公堤西段立李超琼雕像。
李超琼生前,曾为宝山县县令窦殿高(镇山)写过一副挽联:老友语即定评,戆而好辩多真气;近人诗可移赠,死竟无钱是好官。这条严苛的标准,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李巨川,湖南湘阴人。生于上海,长于江苏。有过农村插队、工厂做工、大学任教。1993年起参与中外合作成片土地开发项目苏州工业园区的筹建和早期建设,现已退休。18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著有《芸芸和她的三男》《我们与共和国同龄》《老百姓的小世界》《亲历SIP》《裕廊山下那棵海苹果树》《晚清县令李超琼》等纪实文学作品。有学术专著《千古文章大手笔》。曾在《毛泽东传世语言艺术》《苏州工业园区志》等大型历史文献中担任主编。
李巨川,湖南湘阴人。生于上海,长于江苏。有过农村插队、工厂做工、大学任教。1993年起参与中外合作成片土地开发项目苏州工业园区的筹建和早期建设,现已退休。18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著有《芸芸和她的三男》《我们与共和国同龄》《老百姓的小世界》《亲历SIP》《裕廊山下那棵海苹果树》《晚清县令李超琼》等纪实文学作品。有学术专著《千古文章大手笔》。曾在《毛泽东传世语言艺术》《苏州工业园区志》等大型历史文献中担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