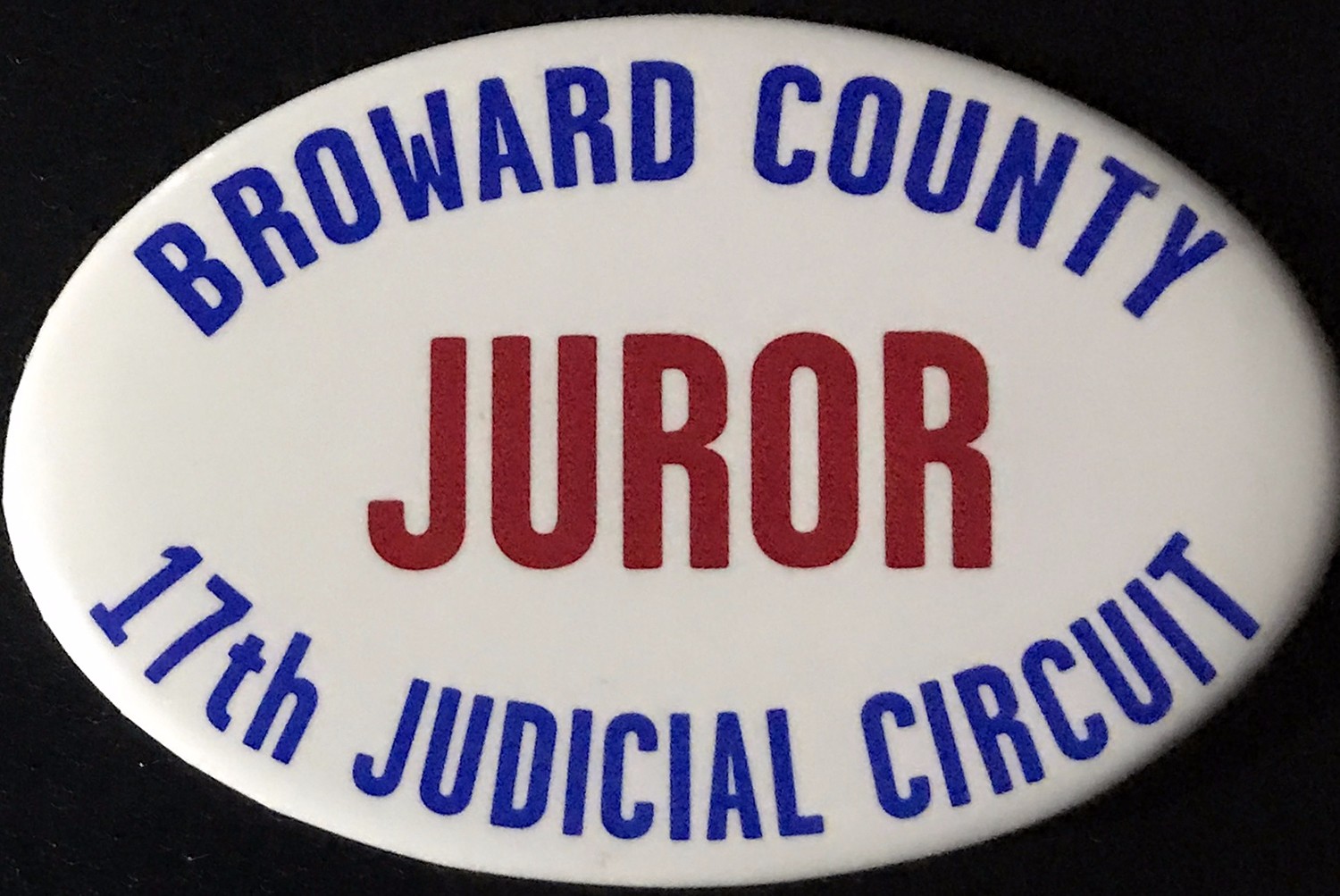按照美国法律,只要是美国公民,就必须履行宪法所赋予的陪审员义务。所有居民都会被随机抽签而收到法院传票,在指定的日期与时间去法院报到担任陪审员。即使卸任的总统,如小布什和奥巴马也都收到法院传票去做陪审员,履行普通公民义务。只有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可以申请豁免本次义务:1)年过70岁);2)在过去一年内,已行使过陪审员义务;3)已不是本地居民;4)有案在身,不能行使此义务。如果无故不去,也不事先说明理由,那可就是对抗法庭的罪名了。
陪审员所涉及的案子可以是刑事案,也可以是民事案,只要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有公民陪审团。可以是联邦法庭的案子,也可以是州巡回法院与县地方法院的案子。如果是州县的案子,由于每个州的法律不一样,所以陪审的规章与流程也都不一样。在佛州,对于刑事案件,陪审团只负责根据检察官的起诉书及所陈列的证据,判断被告是否有罪,什么罪。至于如果有罪,该如何判刑,则是法官的事了,因为牵涉到的法律太多了,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搞得清楚。
(一)甄选
这次收到陪审员传票时,正在中国领教今年的酷暑呢。在指定报到日期的前几天兼程回到了美国。周二那天一大早起来,一身商务便装,直奔几十里之外的第十七巡回法院,在给陪审员专备的停车场泊好车,赶到三楼的陪审员候选大厅,比指定的7点半还早了十几分钟。
大厅内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手持传票的陪审员候选人,男女老少,黑白黄棕,少说也有几百号人。八点半整,“全体起立,尊敬的鲍威尔法官到!”年过七旬的法庭办事员站在一旁高声宣告。全体起立,一位须眉略白的高个子法官身着黑色法官服来到台前,两个大屏幕使得散坐在大厅内每个位子的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做了自我介绍与致了欢迎词后,他开始宣读一堆大道理,无非是公民的职责啦,感谢啦,等等。他退场后,那位办事员煞有介事地宣告“请大家注意了,听清楚我的每句话,我每天在这里讲同样内容的话,已经十几年了,每天都会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反应,我已见怪不怪,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清楚了哦。”接下来她滔滔不绝的讲了一大堆注意事项与每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一天会是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她然后根据传票上每人那独特的序列号开始宣布每个人所归属的法官。
我那一组属于法官西格尔,共有49位候选人。一位职员核对人数后,领着大家去到另一栋楼的七楼,那是西格尔法官的专属法庭。按照庭内座位的编号,由一位法警让人们在庭外按号排好队,然后他向法庭通报,“陪审员进场”。打开门,人们井然有序的进入法庭就坐。每个座位上放有一张提问纸。庭内充满着庄严肃穆的气氛。

县司法大楼
坐在庭内右前方法官席上的西格尔法官,约五十多岁,披着黑色的法官服,首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拿着张纸,分别介绍庭内的其他人员。他右边是一位黑人女性法庭书记官,左手边是配备有特殊打字仪的白人女性速记员。那台打字仪连着电脑,能将速记即时转换成正常文字,并在闭庭后经过整理成为正式的法庭记录。法庭内所有人的英语讲话都会被速记下来。在陪审员与法官席之间有两张桌子,分别坐着那位身着西服,头戴耳机的拉丁裔被告何塞与他的律师。由于被告不懂英文,所以在被告席旁有二位英西同声翻译。同声翻译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所以是二人一组,每20分钟互换。除了被告的答辩需要译成英语,让整个法庭都能听到,其余时间基本是英语译成西班牙语,定向微麦只有被告能听见。与被告桌成丁字型的两张桌子前是州检察院的两名白人女性公诉人,看上去年龄不过30多岁。另外,在法庭门口,有两位拉丁裔法警。
庭内49个候选人里,凭肤色与脸型可明显看出有17个黑人,3个亚裔,其余的就是以白人为主的各色人种。这个与本县180万居民中27.8%是黑人,3.5%是亚裔的比例倒也差得不太远。
法庭书记官接着开始点名。由于人们来自全球各地,语系各不相同,名倒还容易,可是姓却经常念错或念不准,不时得需要向被点到名的询问如何正确的发音,譬如我的姓就很少有人能发得准确的。
“全体起立,将你的右手放在左胸前,请一起宣誓回答:我是美国公民,是本县居民,并且没有由于犯罪而失去公民的权利。”书记官听清了每一个人的回答后,让大家坐下。在美国,说话可以不算数或反悔,但是在法庭宣誓的所有话语都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人民都将宣誓作为极其严肃认真的行为。
书记官接下来让每个候选人自己简要回答那张提问纸上的14个问题:
1)姓名,拼出姓来;2)在本县住了几年;3)工作是什么;4)如果现在不工作,以前的工作是什么;5)有否结婚;6)有几个孩子,分别多大;7)配偶是否工作,什么工作;8)有否做过陪审员:是哪一类,是否首席,案子有否得到裁决;9)家庭成员与亲属中有否被逮捕过;10)家庭成员与亲属中有否犯罪记录,什么罪;11)家庭成员与亲属中有否曾是任何犯罪的受害者;12)有否朋友亲属在执法系统工作;13)有否健康原因使你这次不能履行陪审员职责;14)有否其他原因使你不能担任或公正地做陪审员。
每人轮着一一作答。有些人不愿意在大众面前回答某些问题,特别是上述第9-11个问题,他们就会提出来仅在法官、律师与公诉人面前私下回答。而对于第13-14个问题,借口有困难的可是五花八门,有的说要接孩子,有的说要学校参加考试,有的说已定好出外旅游,有的说要开刀动手术,最离谱的是一位说当他收的传票后就紧张得牙疼,恐怕被选上后会晕倒在法庭,这位并用手捂着牙,引起人们的笑声。我则提出来如果案子在本周结束我可以参加,否则会耽误我的国际旅行。法官、书记官、被告律师、公诉人都各自在事先印好的候选人座位姓名表上备注着有关各位候选人回答的要点,法官并会不时地问话,澄清那些奇奇怪怪的借口与理由。
公诉人与被告律师分别询问了所有候选人,是否认识本次法庭内的人员与即将出庭的证人。得到否定回答后,法官再三强调候选人之间不准讨论,也不得向他人通报陪审过程的任何细节。不知不觉已经下午1点多了,法官宣布午餐休息90分钟。
法警打开门后,候选人们出到庭外,或上厕所,或活动手脚,或打电话,更多是前往法院食堂或邻近餐馆,毕竟正坐几个小时不是那么轻松的。午餐后,法警让所有人按首次排队的次序在庭外排好队,再三嘱咐进去后按原座位就坐。“陪审员入庭”,所有人进入法庭,坐在原位。

法院餐厅
法官将起诉书的标题及案情简介告诉大家:佛罗里达州政府起诉何塞猥亵少女。这仅是起诉的罪名,并不等于被告有罪。而陪审员的作用就是在听取了所有公诉人呈现的证据与证人陈诉后,判定被告是否有罪,有什么罪。法官再三强调,现在所念的起诉书摘要仅作为信息传递所用,具体细节需在选定陪审员后,再一一列出。
接着公诉人与被告律师分别向每一个人询问其对某些法律问题的看法。声音响亮、口齿清楚、颜值颇高的那位女公诉人再三强调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有多少证人证物才能定罪,而有些犯罪基本就没有证人证物。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看法如何。公诉人举的一个例子是,如果有个很坚固的盒子,里面有一只猫与一只老鼠,老鼠没有机会逃出笼子。当打开笼子看时,老鼠没有了。你能否就此判定猫将老鼠吃了?我一听这个例子,就意识到这个案子内公诉人可能证据不充分,所以再三强调推理逻辑的重要性。而那年过半百、彬彬有礼、说话一板一眼的拉丁裔律师,一上来就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为了美国的法制而贡献自己的时间;不管是否被选上,不管最后结论如何,他都感谢每一位候选人。他接着反复强调美国的法制体系是讲证据的,所有结论都必须根据事实与证据并以法律为准绳而得出。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律师也是逐个问话,了解人们对证据重要性与如何信服公证人起诉理由的理解。
公诉人与律师向人们问话的焦点在于如何“超越合理怀疑”。公诉人想要知道的是,如果有充分理由让你消除你对被告有罪的怀疑,你是否会判被告有罪,而律师向人们强调的是什么是合理的怀疑,什么样的证据与多少证据才能彻底超越那合理的怀疑。
四个小时漫长的逐个问答,搞得众人筋疲力尽。法官让大家在庭外等候,他需要与公诉人与律师挑选7位双方都能接受的陪审员,其中6位是正式陪审员,1位是候补。
又是将近1个半小时,其中不断有个别人被叫进法庭,去回答那些其不愿意公开回答的问题。好不容易等到法警出来宣布包括我在内的7位被选上的幸运者,天已黑了。
我们7位陪审员再次进入法庭。我们2女5男中,除了我之外,一位女性菲律宾裔少年网球教练,一位黑人牧师,一位白人汽车保险事故估价员,一位女性白人退休文员,一位拉丁裔学生,一位拉丁裔公司老板为候补的。看来公诉人与律师对族裔的歧见是极其明显的。17个黑人只选了一位,而3个亚裔却选了两位,况且另一位可能是由于再三强调有不可缺席的期末学位考试而没被选上。
西格尔法官首先向大家致歉,从早晨7点多在大厅报道开始,连续12个小时,不但没有一点报酬,每人还要自付午餐费用。他说这个案子根据他的经验,明天从上午10点开始,如果顺利,应该当天可以结束,最晚后天也能结束。如果有谁需要向工作单位或学校证明这几天需要行使公民义务而不能上班或上课,请将邮件地址与收件人姓名头衔交给法警,他会马上发出官方的法院证明。西格尔法官最后又念了一大堆注意事项,譬如不能相互讨论案情,各自独立思考,不能上网查验有关案件或法律,不能对任何人,包括直系亲属,讲有关案件的任何细节。一旦发现,就是藐视法庭的罪名。
法警给每人发了一个胸章,标明是陪审员,法院内的其他人就不能来随便的搭讪问话了,进出法院过安检也不用额外表明身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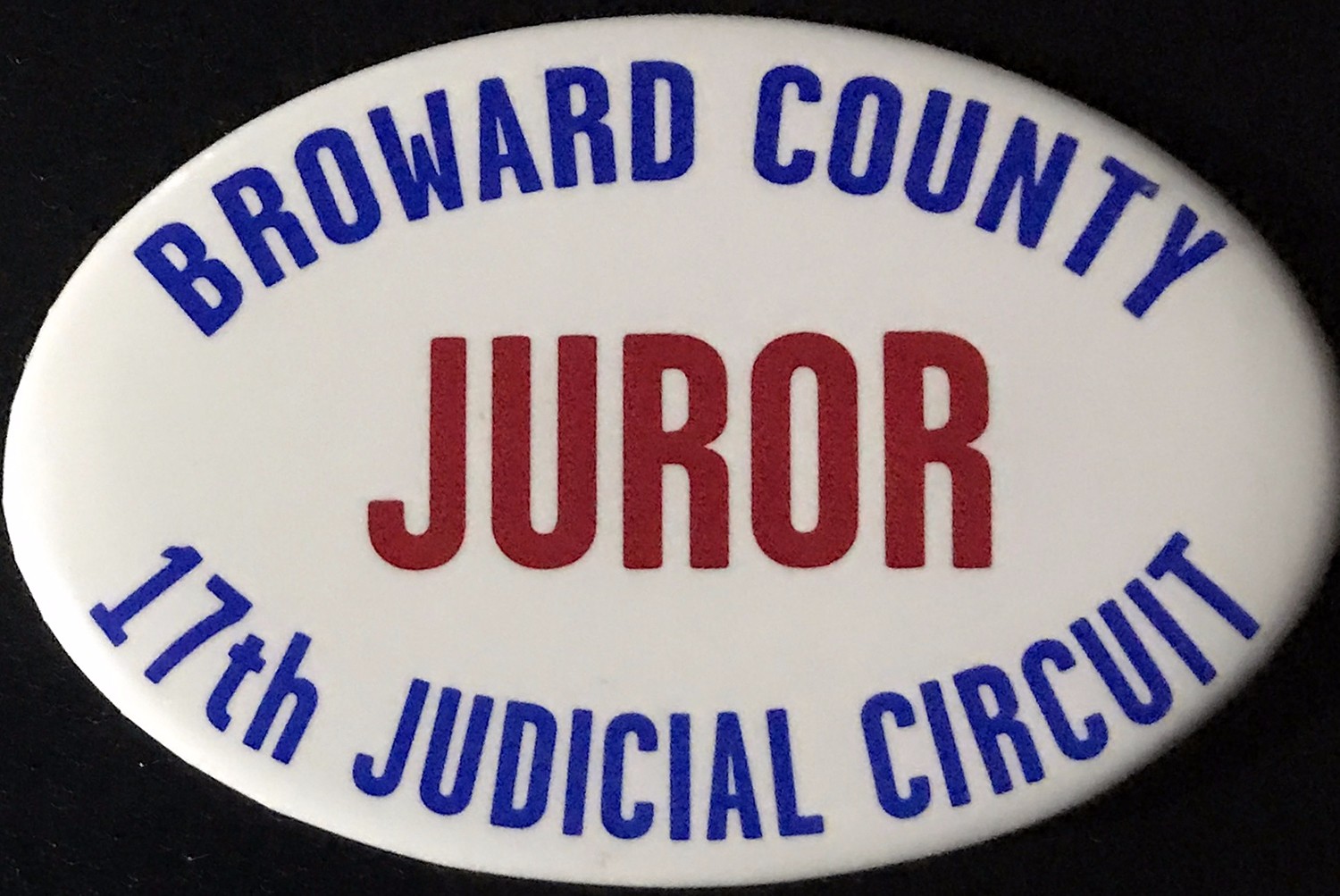
陪审员胸章
(二)陪审
第二天早晨10点,我们7个人来到专门给陪审员准备的套房,里面有洗手间,咖啡机,并且与外界隔音,保证陪审员讨论时不受外面干扰。门外有法警看着,只有他可以敲门,由里面开门。由于尚不知案情,相互也不认识,大家喝着咖啡,吃着法警准备的点心,有的看手机,有的用电脑工作,很少交谈。等了将近1个半小时,才通知我们进入法庭。
庭内还是昨天那些人,法官、书记官、被告、律师、公诉人、翻译,与法警。西格尔法官首先宣布开庭,念了一大堆主要是陪审员的职责、行为条例与注意事项。每个陪审员发一记事本与笔,供在陪审时做些笔记,笔记本只能由本人在法庭内与陪审员套房内使用,不得用于交流,审判完了后必须上缴销毁。
公诉人代表州政府阅读起诉书:被告何塞1981年生,是一位不懂英文的建筑工人。7年前他在迈阿密居住时,认识了刚离婚的朱蒂。朱蒂是本县硬石赌场的客服,有两个女儿,当时11岁与6岁。前夫付着抚养费,每周探望一次女儿们。2011年,被告与朱蒂结婚后搬到了本县,租了一套两居室50平米的小公寓,两个女儿一室,他俩一室。后来又生了个儿子,两年前离婚。
2013年春,大女儿克里斯蒂告诉她中学的闺密,说何塞好几次在晚上去她卧室,无言的将手透过内裤放在她的私处进行抚摸。她的闺密在当年鬼节前夕报警,警察去她家将何塞拘留。从而有了今天这场4年后的审判。
州政府控告何塞犯了猥亵少女罪。为了证明何塞犯了这条罪行,州政府需要证明3点:1)受害人在12-16岁之间;2)被告猥亵了受害人;3)被告超过18岁。其中第一条与第三条从受害人与被告的年龄无容置疑的可以满足。关键在于证明第二条。
那位年轻的女公诉人接着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少女受到性侵的危害性等大道理,陈述了政府是如何从那位闺密的报告中得知案情,并进行了详细调查,最后决定起诉的。果然不出我料,她告诉我们,由于案子的特殊性,没有物证,没有DNA证据,只有受害者的证言,但是她相信陪审员们一定会主持公道,将罪犯绳之于法的。那位被告律师接着上场,再一次感谢被选中的陪审员,强调被告是无辜的,并且几乎胸有成竹地对我们说,你们听完证人们的证词后,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控告几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而我的客户也会自己出来作证,证明他的无辜。这两位的发言将近持续了一小时。已快下午1点了。
午餐休息后开始聆听公诉人及律师对证人们的交叉询问。4位证人先后坐上庭内左前方的证人席。每位证人首先起立宣誓:所说的是真话,而且只有真话。首先上场的是检方证人,朱蒂的大女儿克里斯蒂。18岁的大学生,个子不高,典型的拉丁裔女孩。在公诉人的询问下,她平静地陈诉了从继父闯入她的生活开始,她就不喜欢他,两人经常吵架,而她母亲却总是站在他的一边。这也就是为何何塞在晚上猥亵她时,她不敢声张告诉母亲。促使她终于忍不住对闺密说是因为何塞有次告诉母亲她手机内有打架的照片,而母亲没收了她的手机。想不到这个现在已不是她朋友的闺密去报警了。讲到动情处,克里斯蒂泣不成声。公诉人与律师先后问了她很多问题,当然双方询问的目的与意图是截然相反的。律师询问的重点是在从她的陈述中找出自相矛盾的地方,向陪审员显示她从小就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经常撒谎,讲话的可信度不高。

法庭内素描
在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及发言中,经常会遇到对方起立抗议,或是指责诱导性询问,或是抗议询问范围出格无相关性,不符合法庭程序。法官会立即同意或否决此一抗议,法官也会将控辩双方叫到面前进行庭边商议,统一认识,以便询问能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不会遭到对方不断地抗议。法官这时会打开一个声响开关,使整个庭内充满着白噪声,陪审员与其他人就听不见控辩双方与法官的讨论,但是速记员还能照样将他们的对话记录下来。等到双方回到原位,法官关闭噪音,询问才会继续进行。
接下来的2个检方证人,一位是县警察局当时记录何塞与克里斯蒂口供的警察,一位是主持性犯罪受害者及性侵者心理治疗诊所的博士专家。那位专家并不知道案子详情,是检方花每小时二百美元请来陈诉她的研究与实践结果:75-80%的性受害者不愿向他人透露实情,即使报告透露也会有一个时间延迟。公诉人试图让这位专家来说明,克里斯蒂没有在当时告诉她母亲或其他人是很正常的。而律师则通过对专家的询问,向我们说明这个证人与本案毫无关系,这些研究表明的仅是统计结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她的研究适用于本案。
最后一位是辩方证人,被告何塞本人。由于他不说英文,所以翻译跟着他站在证人席旁,非同步地翻译他的西文与公诉人或律师的英文。何塞说首先他完全没有做过那些被控的行为。他在建筑工地上班,每天6点就得起床,晚上也睡得较早。公寓很小,两间卧室紧挨着,况且朱蒂睡眠很浅,一有响动就会醒。克里斯蒂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特别是当他有次看到她在手机内看色情视频后告诉朱蒂,朱蒂将她的手机收走,引起了她极大的不满。公诉人引用何塞在警察局的笔录来证明何塞曾经说过他与克里斯蒂的关系还可以,但是没有否定他说的其他事实。律师则通过询问,反复地试图证明克里斯蒂与何塞的关系与居住环境都不可能发生所被控的行为而克里斯蒂一声不响,也不惊醒朱蒂。律师并巧妙地通过询问,向我们说明克里斯蒂的生活费是她生父提供的,她完全不会唯恐何塞离开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从而没有理由受到性侵而不吱声。另外那手机事件并不是因为打架照片,而是儿童不宜的色情视频,从而佐证了克里斯蒂说的不是事实。
在整个交叉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除了仔细听及做些笔记以外,一言不能发,有任何疑问意见也都不能提,当然也不能相互交谈。不知不觉又是下午6点多了。西格尔法官再一次向大家致歉,说看来明天还得麻烦大家,但是明天的进程就看你的讨论进度了,言下之意就是证人都问完了,就等陪审员下结论了。
第三天早晨10点到达陪审员套房后,由于案情已明了,大家自然的开始谈些自己的想法。不知谁先开了个头,大家开始抱怨这个过程的冗长,都说我们已花了两天时间,这些人这么啰嗦,西格尔也是很会拖时间,每天搞得我们这么晚。我们今天讨论需要快一些,早些结束。
10点半,我们被叫进法庭,聆听控辩双方的总结性发言。
这个总结发言对双方都有时间限制,而他们都控制得很好,几乎都是一分钟不差,看来都是老手,不知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公诉人先发言15分钟,律师接着讲了半小时,最后公诉人再用15分钟结束了整个过程。这中间还遇到好几次的庭边商议。双方各自强调他们的观点:控方认为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有物证与他人旁证,对发生在房间内的罪行,受害人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克里斯蒂昨天的哭泣不是伪装的,只有真实地受到过伤害,才会如此地动情。辩方认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无法超越合理怀疑这一定罪的门槛。双方的话其实都是说给我们听,谁能使我们信服,谁就打赢了这场官司。
控辩双方回到座位上。西格尔法官宣布州政府指控何塞犯有猥亵罪,或较轻的伤害罪。接下来就是陪审团评议,也即由陪审员们通过讨论最终作出裁决的互动过程。西格尔法官给陪审员的一个最主要的指导就是只要有疑问,有合理的怀疑而不能跨越,就不能裁定被告有罪。所有陪审员必须得出一致结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则必须继续讨论下去。如果经过很多努力,还是不能得到一致意见,那这次审判就无效,整个过程必须换陪审团而重新开始。陪审团在这个案子中必须在下述三个选择中达成一致的选择意见:1)猥亵有罪;2)伤害有罪;3)无罪。
(三)审议
午饭后,我们6位陪审员将手机关机并上交给那法警保管,进入陪审员套房进行评议。由于我们无人缺席,所以那位候补的就完成了他的使命而离开了。从此任何人不得进入陪审员套房,那位法警也只有我们用连通门外的红铃招呼他并开门才能站在门口,而不能踏进房间。如果我们达成一致协议,则连按两次红铃,有其他事按一次。
桌上除了我们每人的笔记本外,有几张白纸与裁决书,上面印着案子的标题以及三个选项,即1)猥亵有罪;2)伤害有罪;3)无罪,下方是首席陪审员的签字处及日期。
大家坐下来后,首先是推选首席陪审员。首席陪审员的作用是在评议过程中掌握进度,控制场面,最后在裁决书上签字,并在法庭代表陪审团向法官递交裁决书。由于那位黑人牧师是当初49位候选人中编号的第1号,所以大家就推选他做了首席。
由于已经是第三天,所以大家都希望尽快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尽管没有明说,但是大家都不希望由于一个人的不同意见而拖延时间。

法庭内部
首先每人提一个选择,并说明自己的看法与理由。连我在内的四个人很干脆的选了无罪。都认为证据不足,那个警察与专家的证词基本可以被忽略,因为与案情没太大关系。而仅有克里斯蒂的证词不能说明此事一定发生过,况且克里斯蒂与何塞两人的证词是典型的你说他说,双方的证词都有经不起推敲的不稳定或不符逻辑的内容。
我提出个奇怪的现象,为何与此案密切相关、最能作为旁证的朱蒂与那位闺密竟然没被检方请来作证人。特别是朱蒂已与何塞离婚,她完全可以前来作证的。这么简单的案子为何拖了三年多?作为刑事案,并不需要等克里斯蒂满18岁才能开庭起诉的。
其他几位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那位保险估价员说他在事故现场往往可以通过汽车实际受损程度来判断众人所述事故过程的真实性。检方所控的事实如果真的发生过,而何塞没遭到克里斯蒂的任何反抗,竟然会每次仍只做同样的无声猥亵,而没进一步的动作?那位菲裔也说她整天与孩子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与思维过程,如果是反复发生的,一定会忍不住说出来的,而母亲往往是第一个倾诉的对象,在这案中似乎没听说她们母女的关系很差。那位白人退休文员说,她三个小孩都在法律系统工作,她知道一个无辜的人被冤枉是多么的不幸,何塞如果被判猥亵有罪入狱,像他这么瘦小,可能没多久就在狱中给那些暴力罪犯给打死了。
那位拉丁裔学生一开始还有些犹豫是否该判他伤害罪,继父性侵继女是最常见的家庭隐形犯罪。可是如果克里斯蒂没受到过性侵,她没有理由还要出来作证,因为将何塞投进监狱,并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在听了其他几位的疑问并众人的进一步讨论后,特别是克里斯蒂与何塞两人对手机事件中的手机内容描述不一致,使人无法消除克里斯蒂谎报事实的怀疑,他也改变了主意,裁决无罪。
剩下来只有那位牧师还是认为何塞有罪。在他的牧师生涯中,每天都有人向他忏悔,而这中间很多都是继父母对孩子的各类不当行为。他相信何塞真的做过所被控的行为。这类行为往往由于双方在家庭中的不对等地位,受害人不能或不会告诉其他人,特别是当孩子年龄很小时,她们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些行为是犯罪。所以牧师从直觉上认为何塞干过,应该判他有罪。但是他也承认很多陈述的事实不符合一般常理,譬如这么小的公寓,怎么可能朱蒂一点不知情,克里斯蒂当时还毫不声张?
这时讨论的重点就在检方的证据能否使我们超越合理的怀疑。我们的怀疑就在于那些所控的犯罪行为中不符合常理的细节,为何检方不找直接相关人士来作更有说服力的证人。我们两天来所听到的无法使我们迈过合理怀疑这一坎。牧师还试图选较轻的伤害罪,但也被众人给说服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最后我们6位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无罪。牧师在裁决书上的第三个选择打了勾,签上了大名。我们大家都嘘了口气,似乎放下了一副重担,也为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达到一致意见而相互祝贺。
(四)裁决
那位估价员按了两下红铃,打开了门。法警站在门口,“你们达成一致意见了?”得到明确答复后,他让我们稍等片刻,关上了门,去向法庭报告。过了一会,他重重地敲门,我们打开门,在他的引导下进入法庭,各人拿着笔记本,那牧师则还拿着裁决书,仍按原位坐下。
明显地感到控辩双方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裁决结果,特别是那被告,脸色苍白,紧张兮兮地看着我们,颇有些盼望又带着些绝望的神色,他的命运马上就要被宣布了。按照法律,如果猥亵罪成立,最高可受5年牢狱之苦,那他这辈子就算完了。如果无罪,他不但立享自由,而且律师还很有可能为他反告政府要求赔偿失去自由的代价。
“谁是首席陪审员?”西格尔法官问到。
“是我,尊敬的法官先生。”牧师回答。
“请将评议裁决书递上来。”
法警将牧师递给他的裁决书传给了西格尔法官。他看了一眼,将它递给了法庭书记官。两位公诉人、律师与被告站了起来,听候那书记官宣读裁决书:
“陪审团经过评议,一致裁决,被告何塞无罪。首席陪审员XXX,签字。2017年8月31日。”
听到此一裁决,两位女检察官交换了一下眼色,脸上露出几丝冷笑,但绝无失望的意思。可能公诉开庭是她们的例行公事,赢与输,每天都在发生,又与他们个人没太大关系,所以没有所谓的。那位律师则好像对无罪结果早在预料之中,一点没有动容,侧过身来,面带微笑的与何塞握手。何塞可能是太激动了,脸上抽搐着,好像欲对律师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
“公诉人,是否需要逐个问一下陪审员的选择?”西格尔法官问道。
“是的。”其中一位答道。
那书记官按着陪审员编号逐个报姓名询问我们是否同意第三选择,我们每个人都回答是的。
西格尔法官致“闭幕词”。他再一次感谢所有陪审员在过去几天内为维持美国法制所履行的义务服务,讲了一通大道理,并为每个陪审员颁发了由首席法官作证、他签名的第十七巡回法院感谢证书。法警还回各人的手机,并将笔记本内有记录的部分撕毁收缴,取回了那枚陪审员胸章。庭内全体人员起立,目送法警将我们引出法庭。
三天挺有意思的陪审就此终结。那几位陪审员“同事”这辈子大概也不会再见到了。而至少在一年之内,我是不用再履行此一义务了。

法院发给陪审员的感谢证书

 良人,本名许人良,为77级复旦大学毕业生,80年代早期前往美国,在杨振宁任教的学校留学,获博士学位。曾在多家跨国企业内任研发、市场与管理等职位,为国际标准化组织资深专家。他长期在美国弘扬中国文化,以双语向世界介绍美国文化。出版有近百篇学术论文、多部英文与中文的专业及文学著作,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良人为笔名。
许人良现任中国一家美资公司的总经理与美国大西洋中医学院董事长,为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并在中美多个专业化组织内任职。
良人,本名许人良,为77级复旦大学毕业生,80年代早期前往美国,在杨振宁任教的学校留学,获博士学位。曾在多家跨国企业内任研发、市场与管理等职位,为国际标准化组织资深专家。他长期在美国弘扬中国文化,以双语向世界介绍美国文化。出版有近百篇学术论文、多部英文与中文的专业及文学著作,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良人为笔名。
许人良现任中国一家美资公司的总经理与美国大西洋中医学院董事长,为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并在中美多个专业化组织内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