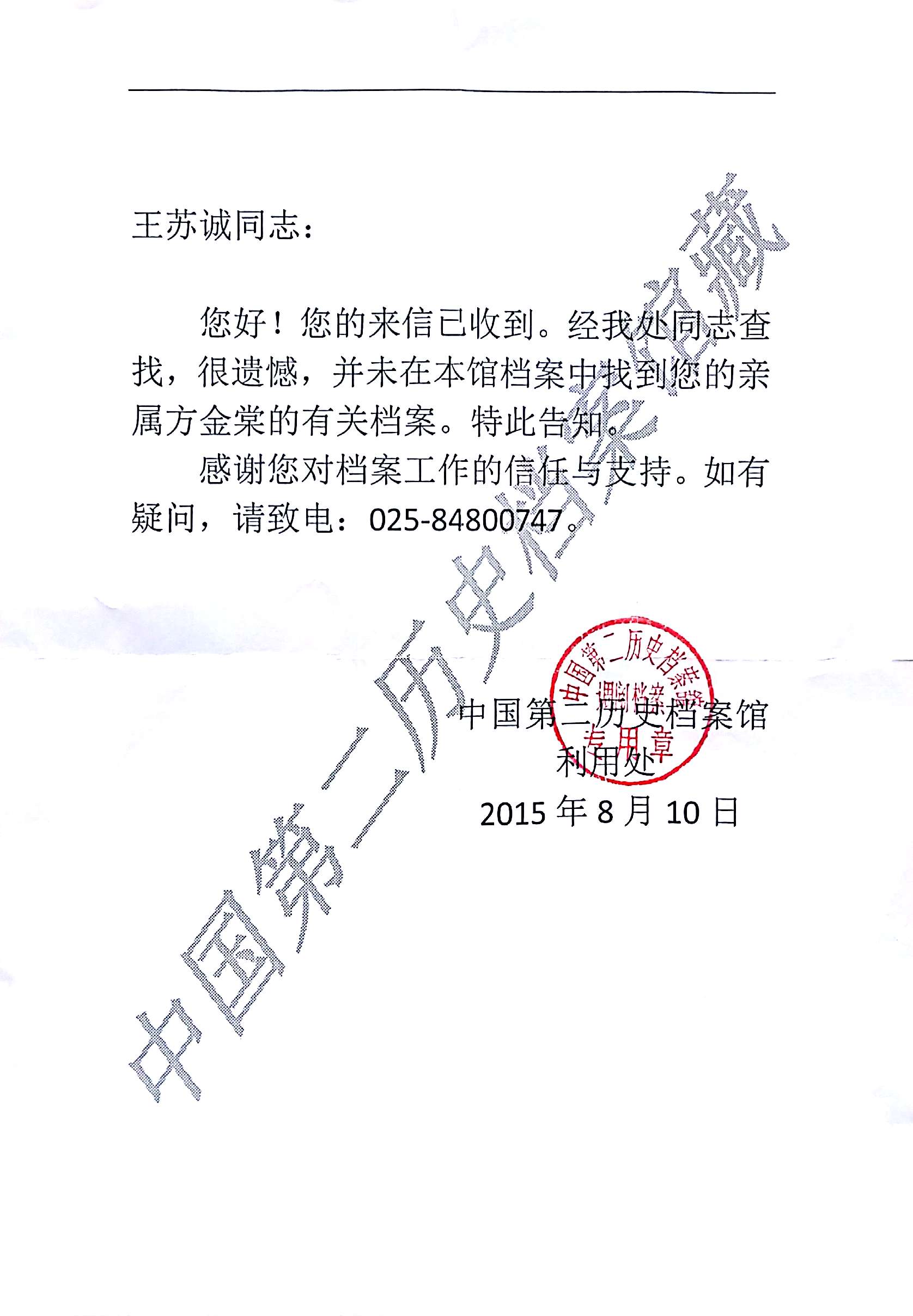我一直将上海东部的杨树浦和南部的十六铺这两个地方,视作自己人生中的两极。杨树浦,因杨树浦港综贯区境南北而得名,为此,杨浦区曾经也称之杨树浦区。十六铺,据传是晚清咸丰年间为防御太平军进攻,当时的上海县将城厢内外的商号组建了一种联防的铺”。因十六铺在所有的铺中规模最大,也就逐渐成了这块区域的地名。从杨树浦到十六铺,上海这一东一南两个地理区域特征十分鲜明的地标,串联起了我幼年、童年、少年足迹,从而在我的心灵中留下永远难以忘怀的情结。
外白渡桥,我的外婆桥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是几代上海小囡个个都会吟唱的一首童谣。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的那座百年老桥外白渡桥,应该就是几代上海人的“外婆桥”了。我居住在杨树浦,每次去看望居住在当时的南市区十六铺附近的外公、外婆必定要穿过外白渡桥。因此,外白渡桥对我来说,更是超越童谣意义上的一座名副其实“外婆桥”。
孩提时因父母工作、居住都在杨浦,正值壮年的父母为了“废寝忘食”建设社会主义,便将我从小就寄养在住在南市区的外公外婆家,在荷花池幼儿园度过了一段欢乐时光。
外公外婆的家位于南市老城厢的王家嘴角街16弄的过街楼上,那条弄堂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楼下的一条台硌路上不仅有闻名的紫霞路菜场,还有老虎灶、点心店、烟纸店、煤球店等,每天都是在穿街走巷各式小贩的吆喝声中迎来新一天曙光。
清晨时分,当我还在睡梦之中,楼下的小菜场已经传来阵阵喧哗声。早已起床的外公便拎着两个热水瓶到家对面的老虎灶泡满开水,然后和外婆将开水注入各自的紫砂壶后,手捧紫砂壶端坐在弄堂口的一张小桌边,微笑地注视着进出弄堂的左邻右舍及熟悉和不熟悉的菜场营业员、菜贩。因为外婆是里弄小组长,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们,均会不停地和外公外婆打招呼:“王家老爹、王家姆妈早上好!”外公外婆也不断向路人点头:“李师母,侬今朝买点啥小菜?”“陈太太,勿要忘记下午到里弄开会噢!”
每当夏季来临,当石库门弄堂里响起阵阵“栀子花,白兰花,五分洋钿买一朵……”的叫卖声,外婆都会买上几朵白兰花,别在她那件咖啡色香烟纱衬衫的纽扣处,袭人的香气在夏日傍晚余温的空气里氤氲着。此时,躺在竹榻上乘风凉的我,边陶醉于白兰花的芬芳,边享受着外婆用蒲扇摇出的阵阵凉风,那一刻,绝对是我一天里最为惬意的时光。如今回想起来,这真是一幅充满上海弄堂市井气息的“清明上河图”。

1989年4月29日作者夫妻和外公外婆在婚礼上合影
一直到了读小学的年龄,我才回到杨浦的家,但是每个周日,父母都会带着我和弟妹一起到外婆家“度假”。有时,我也会独自去。那时上海的道路交通还比较落后,从杨浦区到南市区只有一条25路电车。每次到外婆家都是先乘坐59路公交车到军工路、平凉路,然后换乘25路电车,直接抵达十六铺终点站后,然后步行穿过小东门,沿着复兴东路,走到王家码头路,再拐到紫霞路,就到外婆家了。
25路电车是现在已经绝迹的那种铰链式电车,从杨树浦到十六铺的数十公里路程显得非常漫长,但一旦电车驶上外白渡桥开始进入外滩后,我的神经便会立即兴奋起来。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挤到靠近车窗的位子,探头向外看风景。黄浦江面缓缓驶过的轮船、矗立在外滩的上海大厦、海关大楼等素有万国建筑博览群之称的那52幢风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尤其是坐落在外滩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解放后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门口的那一对威风凛凛的大铜狮子,和大楼前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是我百看不厌的经典“风景”,每次都会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过节般的欢乐。一旦从车窗里看到外滩气象信号塔巍峨身姿时,便知道十六铺快到了,外婆家也快到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向车门边挤去。因为,外公外婆早已烧好美味佳肴等着我去大快朵颐啦!每次得知我要去看望他们,外婆一定会反复叮嘱外公“老头子,明早翔翔要来哦,侬去菜场买点好小菜烧烧啊!”
寻梦王家嘴角街
上世纪90年代初,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王家嘴角街。十六铺、董家渡、小南门等儿时流连忘返的地方,也只是偶尔走过、路过而已。随着2000年6月南市、黄浦两区合并后,南市区就成了一个历史地名,渐渐被人淡忘。但“南市”对我依然刻骨铭心。
2013年2月13日,春节的大年初一清晨,当整座城市还在一片宁静之中时,我已驱车陪着父母来到了自己童年曾经生活过的原南市区王家码头一带的老城厢区域。今天,我是专程陪伴年迈的父母来寻找他们的乡愁。对我而言,亦是来重温自己孩提时代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童年旧梦,寻觅外公外婆当年在此留下的印迹。已经年近八旬,从小在南市老城厢长大的母亲,更是有着一种寻根的情感,这是深埋在她心底许久的一个愿望。尤其是听说随着南外滩的开发,整个董家渡地区都将拆除,南市老城厢一排排石库门风格古旧建筑的不断消失,我和父母的这个愿望变得愈发强烈和迫切起来。每次回父母家,母亲就要说:“啥辰光带我到王家嘴角街兜兜看看啊!”。

父母的金婚纪念
其实,我的工作单位离开南市老城厢并不远,且同属现今的黄浦区,也曾经好几次路过那里。但不是因时间紧迫匆匆而过,就是因大规模的旧区改造,使我找不到旧址而迷路,只得悻悻然地无奈返回。这次是下定决心,利用春节长假的机会,抽出时间静下心来陪同父母到“王家嘴角街去兜兜看看”。
没料到,这次我依然是迷路了。原本非常熟悉的台硌路早已消亡,最终经过几位路人的指点,车子七拐八弯地终算停在了王家码头路。这里就是曾经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充满上海市井气息的南市老城厢吗?这里就是儿时外婆挥动蒲扇,我躺在竹榻上乘风凉的王家嘴角街弄堂口吗?望着眼前这片儿时非常熟悉的土地,如今却早已是“物是人非”,周围的一切成了一片拆迁工地的废墟和瓦砾。放眼望去,只有几个外来务工者的小孩在一排排待拆迁的房屋前嬉闹,不由深为怅然,我的记忆闸门伴随着父母对往事追忆的阵阵叹息声中渐渐打开……
外公王生才、外婆韦兰英是从小就生活在南市老城厢的“老土地”。对于他们年轻时代的经历我并不了解,只是偶尔听母亲说起,他们解放前靠做点小生意谋生。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外公以小业主的成分进入南市区服装鞋帽公司工作,外婆则在居委会做里弄工作。
1956年母亲经亲戚介绍与父亲认识后,1957年在小南门“一家春”饭店请亲朋好友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在父母保存的老照片里,有一张他们谈恋爱时在蓬莱区(南市区前身)西藏中路97号大美照相馆拍摄的彩色照片。这张以人民广场和国际饭店为背景,用印花硬板纸作衬底的人像艺术照,应该是父母定婚照吧。睹照思人,我随即想到那张被无数网民誉为“民国无名女神”李伟华的老照片,其实,我们的父母都有曾经绽放过的青春。年轻人,找出家里的老相册吧,所谓的男神、女神就在我们的身边。

1956年父母摄于西藏中路97号大美照相馆定婚照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外公外婆在他们那个年代中,应该是属于有品质、有腔调的老人。这种品质与腔调不仅表现在他们总是喜欢各自端上一把藤椅坐在王家嘴角街弄堂口,手握一把紫砂壶细啜慢饮地“浏览”路人时的那种泰然神态,以及日常衣着上的考究等外在上,同时也渗透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与旁人的接触和谈吐中。外公说话时的那副冷面滑稽面孔,总会引来众人捧腹大笑。
外公外婆对母亲学习教育十分重视,解放前,他们克服困难,将年幼的母亲送到一所教会学校读书。1951年,母亲十六岁时,他们便把母亲送入一座私立补习学校学习会计专业。1956年,年仅21岁的母亲,已经在南市区的天佑群学会小学做老师。可天性不安分的母亲,是个性格有点任性的女性。不顾外公外婆劝导,执拗地要外出闯荡一番。为此,经常和外公外婆“大吵大闹”。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西安“二九七”电校来上海招生的消息后,便瞒着外公外婆,悄悄地从家里偷出户口簿去报了名,甚至还擅自将名字王根娣改成王苏诚。为了让母亲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尽管外公外婆内心有一百个不愿意,但依然挥泪“放行”。殊不知,母亲是两位老人的独生女啊!他们怎么会舍得让宝贝女儿远走高飞呢?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在我奔赴跃进农场前夕,外婆和母亲特意带着我到小南门的一家服装店,为我买了一件当时颇为流行,且价格昂贵的涤卡中山装。而我在农场使用的那只木箱子,也是外公外婆家里的,这只箱子现在还保存在父母家中。
1976年春节,第一次从崇明跃进农场回市区过年,我用节省下来的工资买了崇明小毛蟹、甜芦粟等,然后绕道从崇明牛棚港坐船到江苏海门,再从那里坐船到十六铺码头。下船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外公外婆家。一走进熟悉的王家嘴角街,我就大声说道:“外公外婆,翔翔现在做生活赚钞票了,买点东西给你们吃吃。”他们开心得笑不拢嘴。1977年在市商业学校读书时,在小南门一家老字号南货店会计室实习,每天午饭都是到外婆家吃的。他们总会烧好我喜欢吃的菜肴,笑眯眯地坐在桌边,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吃着。
董家渡、小东门、小南门、王家码头路、王家嘴角街,有着我太多、太多的童年记忆。今天我徜徉在这片十分熟悉,如今却又非常陌生的土地上,心中默默念唠着:王家嘴角街16弄到哪里去了啊?当年和我共同嬉闹的小伙伴们,他们又在哪里呢? 欣慰的是,经过一番仔细寻找,我和父母终于在一幢已拆除的老建筑的墙面上,竟然发现了残存的一块王家嘴角街路牌。我欣喜若狂,立即像一个考古学家般拿出相机拍了下来,并给父母在路牌下拍了张合影。那一刻,我绝对感觉是完成了一件抢救“历史”的伟大使命。当时动过把王家嘴角街路牌从墙上撬下收藏的念头,但最终为避偷盗之嫌而没有下手。如今想来,真是一大憾事。


2013年2月13日父母在王家最角街旧居路牌下留影
梦醒时分泪婆娑
白相城隍庙,是我们这代人孩提时代的梦。成家后,曾经连续几年的除夕之夜,我都会携家人吃罢年夜饭后,兴致勃勃地驱车赶往海内外久负盛名的上海老城隍庙参加祈福游园活动。当疾驶的车子穿行在挂满大红灯笼和鞭炮声此起彼伏的大街小巷时,童年时代外公外婆带领我白相城隍庙那一幕幕美好情景就会在眼前浮现。
那些年的除夕夜,在王家嘴角街的弄堂口,我和小伙伴们放完鞭炮,听到外婆那句:“翔翔,好早点睏觉了,明朝带侬去白相城隍庙。”这句话,就会兴奋得睡不着觉。殊不知,在那个年代,对于我这个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杨浦区“小鬼头”来说,能够去白相一趟城隍庙,简直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旅游啊!
大年初一早上,外婆替我穿好新衣服,并在衣袋中塞了个红包。然后,我们和外公外婆挤上公交车向城隍庙赶去。一路上,每见到一个熟识的小伙伴,我都会大声说道:“嘿,今朝阿拉要去‘白相’城隍庙啦!。”望着小伙伴们流露出来的羡慕的目光,我走路的脚步也格外地雄纠纠、气昂昂。
拐进方浜中路,已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人流、车潮使得这条狭小的马路充满了旺盛的人气。走进城隍庙,仿佛来到了一个欢乐的世界,眼眶里“装满”了兴奋与新奇:芳香扑鼻的五香豆、晶莹欲滴的梨膏糖、五花八门的京剧脸谱、巧夺天工的剪纸,吃得我嘴“累”,看得我眼酸。虽然那时的我,还不明白什么叫“中国元素”,还“读”不懂外公外婆脸上灿烂的笑容,可是,稚嫩的童心里却早已知道,这,就叫“过年”。
岁月,尽管一如既往地在无情地流逝。但作为一个华夏子孙,不管历史发展到了那朝那代,对列祖列宗的敬重、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爱,将会是永远世代相连、脉脉相传。如果外公外婆能有幸活到今天,两位老人家依然会笑眯眯地说:“翔翔,好早点睏觉了,明朝带侬去白相城隍庙。”率领小辈们浩浩荡荡地去白相城隍庙。
天若有情天亦老。步入高龄后的外公外婆外出越来越困难。原先,逢年过节他们总是要乘坐公交车到杨浦父母家,以后因行走不便,便减少外出了。那时我在杨浦区审计局工作,局里有一辆上海牌轿车,局领导订出制度,谁家里有困难,需要用车的可以申请使用。为此,好几次我都是用审计局的轿车,将外公外婆从南市区带到杨浦区的父母家。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乘坐轿车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记得那辆上海牌轿车停在外公外婆的楼下,周围的邻居看到我搀扶外公外婆上车,无不夸奖道:“翔翔,侬对外公外婆真好啊!”。此刻,外公外婆便笑道:“阿拉现在享翔翔福了!”
外公外婆年龄不断增大后,身体状况也逐渐每况愈下。我经常从杨浦区赶到南市区,为他们做点擦地、买煤球等体力活。每当我踏进房门,看到两位老人或对坐在桌旁玩麻将,或捧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静静地聆听戏曲节目。那一幅幅寂寞的场景,就会让我陡生伤感之情:“外公外婆啊,你们真的是老了,现在该是我‘反哺’你们的时候了!”
外公外婆整天捧在手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电池盖摔坏过,可是他们舍不得买新的,只是用胶布封扎了一下。我多次提出要给他们买台新的,外公总是双眼一瞪,厉声呵斥:“翔翔侬迭只小赤佬,算侬现在赚钞票了是伐?省点钞票以后结婚派用场!”
后来我在十六铺一家百货公司看到一款新出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非常适宜老年人使用,便毅然买好后给他们送去,谎称是自己的一篇文章获奖的奖品,外公外婆才“笑纳”了。
再后来,父母实在不放心年逾八旬的外公外婆独自居住在南市区,最终经过反复劝说,他们才同意搬到佳木斯路和父母一起居住,并把户口也迁移过来。因为这时,上海市政府开始向高龄老人颁发尊老社会一条龙服务的优待证。外公外婆拿到了户籍所在地的杨浦区长白街道颁发的高龄老人优待证。从此他们便成为杨浦区的“移民”。这种上海市第一代高龄老人优待证,应该就是如今敬老卡的雏形吧。


外公外婆的老人优待证
年迈的外公外婆从居住了一辈子的十六铺,晚年移居到杨树浦,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艰难的“转身”。但他们依然身在杨浦,心在南市,时刻还惦念着弄堂口的老邻居们。每过一段时间就必定“命令”我带他们到王家嘴角街的老宅住上几天。那些左邻右舍的老邻居看到王家阿爹、王家姆妈回来了,都会聚拢上来嘘寒问暖。站在一旁搀扶着外公外婆的我,望着两位老人甜蜜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乡愁吧!
撰写此文时,为唤起自己更多的记忆,我翻找出了许多外公外婆与我和父母的老照片。那张我结婚时,外公外婆坐在新房里的照片,从他们笑呵呵神情上可以看出,此刻两位老人是多么开心哦!当看到那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给母亲和外公外婆在南市区王家嘴角街旧居拍摄的三口之家合影照,不禁泪眼婆娑:“外公、外婆、姆妈,你们终于又在天国团聚了,你们在那里生活的好吗?”无数个寂静的夜晚,遥望着窗外的星空,我总会喃喃自语。

八十年代末母亲与外公外婆在王家嘴角街旧居合影
外公王生才生于1904年4月12日,1991年4月28日病故。外婆韦兰英生于1908年12月6日,1992年1月19日病故。他们的寿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应该也算是长寿了。2015年9月26日,亲爱的母亲也与世长辞了。他们虽然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但他们慈祥的笑容,始终镌刻在我的心灵。然而,此刻,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的外公外婆并不是我母亲的亲生父母。他们是我母亲的姨母、姨父,这在我们家并非是秘密,母亲很早就告诉了我。因为外公外婆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母亲的亲生父母便将出生不久的她过继给了外公外婆。从此,母亲便成了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这件事,对我来说,也就是听过而已,外公还是我的外公,外婆还是我的外婆。
晚年的母亲始终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寻找到自己亲生父母身世等档案资料。她对我说,外公外婆曾经告诉她,其亲生父亲的名字叫方金棠,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亲生父亲在奔赴抗日战场的前夕,匆匆将其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外公外婆抚育。此后,亲生父母便杳无音讯。她对亲身父母的记忆,只有那张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她一周岁时,亲身母亲抱着她的合影照片。
为此,母亲曾多次嘱托我“想想办法”。

母亲对亲生父母的记忆,只有那张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她一周岁时,亲生母亲抱着她的合影照片
面对母亲迫切的寻亲情结,我虽想尽办法,还是爱莫能助,无计可施。可是,在母亲去世后,整理她的遗物时,我看到一封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给她的回信。原来母亲得知该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开放了抗战时期失踪、牺牲人员名单消息后,特地写信去查询自己亲生父亲方金棠信息。2015年8月10日,当母亲收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无此人”的回信,一个多月后便带着永远的遗憾走了。
2016年清明节前夕,我们全家专门将外公外婆的墓园重新修葺一新。站在墓碑前,我点燃一炷心香,捧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那封信件,欲哭无泪:
“姆妈,难道是你亲生父亲方金棠和外公外婆在另一个世界召唤你吗?你和他们分别这么久了,他们思念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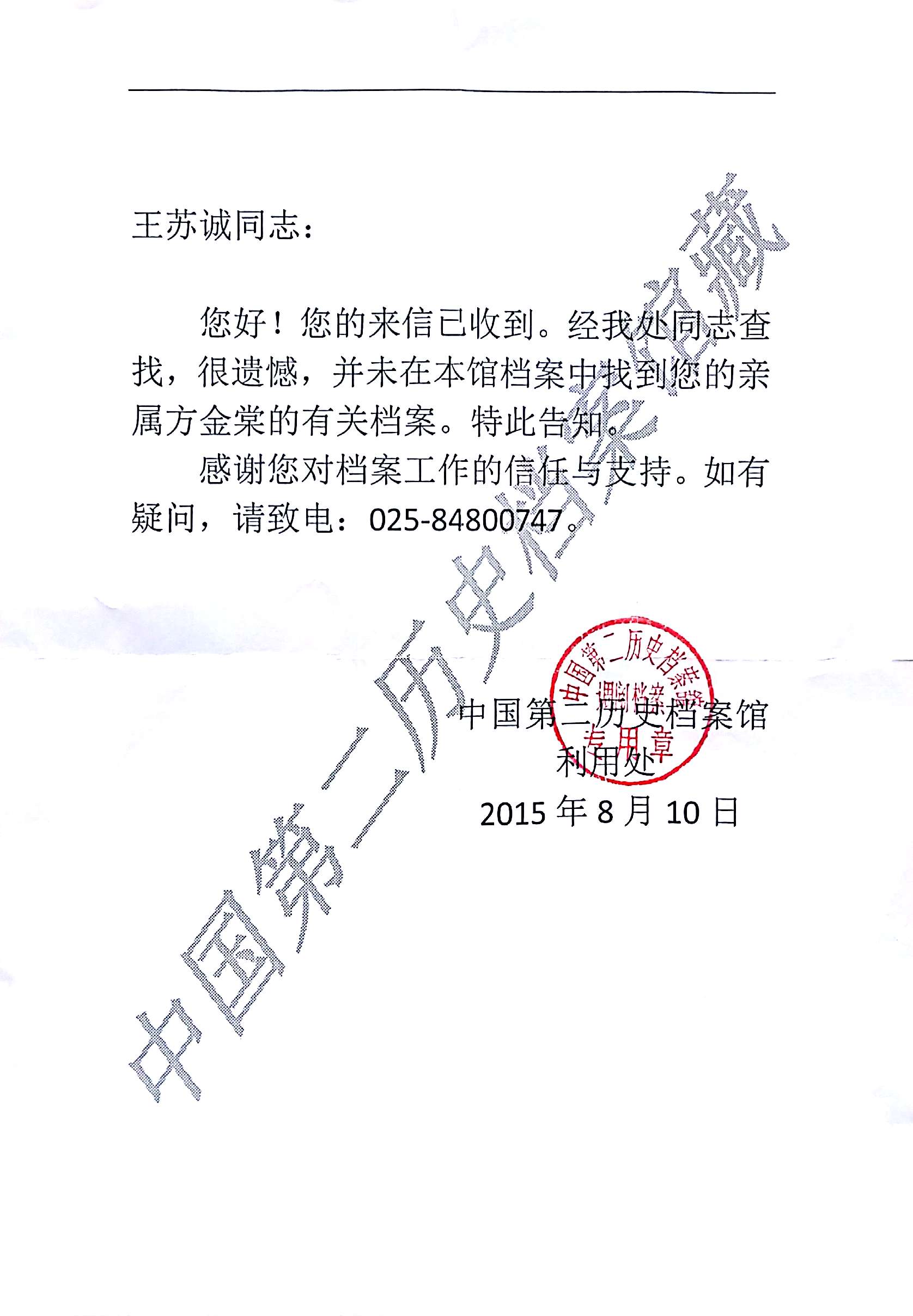
201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给母亲的回函
今天,上海这座城市在飞速成长。王家嘴角街这条石库门弄堂早已夷为平地,董家渡这片土地很快就将崛起巍峨的南外滩,可我还是期望能在这里留住一些南市老城厢的基因与文脉。因为这里每一条石库门弄堂里都蕴含着故事,都有着几代上海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有位建筑学家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一个城市如果都是崭新的,这很难想象。“城市是有温度的,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这两句话说得真好,但我觉得还是说得稍许晚了点。因为,很多、很多石库门老建筑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
杨树浦是上海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十六铺则承载着上海滩厚重的历史记忆。年轻时的母亲,从十六铺老城厢嫁到杨树浦的工人新村。孩提时的我从杨树浦跨过外白渡桥来到十六铺,晚年的外公外婆又从十六铺跨过外白渡桥来到杨树浦,或许这就是生命的轮回吧。

1975年作者在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汇合处留影

 刘翔,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上海市公安局。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成教院政教系,获得法学士学位。自1982年以来,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数百万字。出版有散文集《吃素者说》《刘翔来了》,报告文学集《为警亦风流》,系列纪实文学集《上海大案》5本等。
刘翔,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上海市公安局。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成教院政教系,获得法学士学位。自1982年以来,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数百万字。出版有散文集《吃素者说》《刘翔来了》,报告文学集《为警亦风流》,系列纪实文学集《上海大案》5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