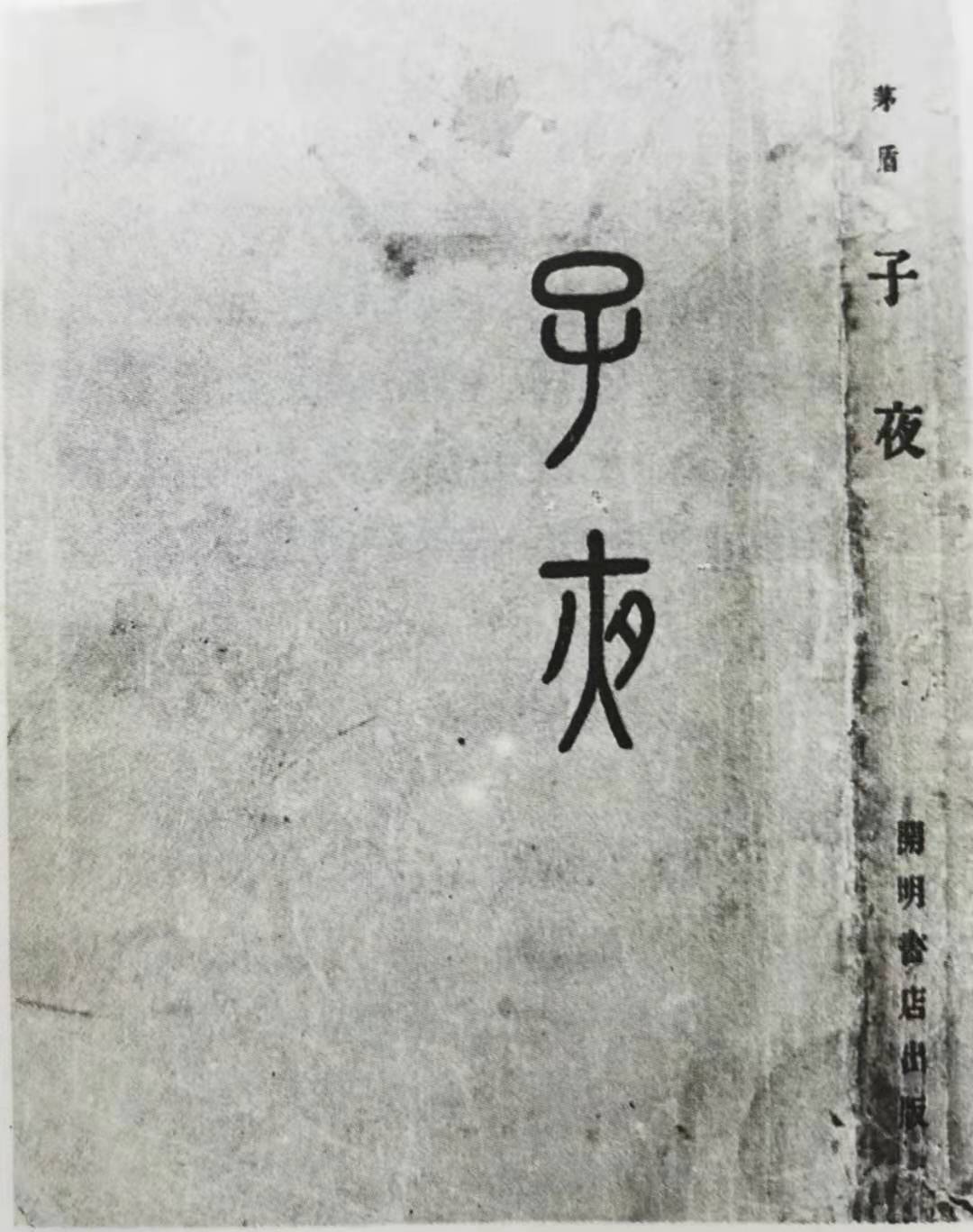“钟英”是当时中央的化名,陈独秀给我的信总是署“仲甫”或“实庵”,一般的通知报告,非陈独秀亲笔信件,都是署钟英,……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1953年8月20日
中共中央撤离上海
到中央苏区去,1932年6月从苏联归国抵沪的董必武就这样向组织请求,7、8月间获准动身前往。事实上,临时中央成员内心这一愿望也日趋强烈,上海已成危城。这年5月,临时中央派邓颖超去中央苏区。此其间,陆定一被苏区中央局重新派回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干事,可见其在那里是有多么的不合时宜。
屡受中央批评的江苏省委大出昏招,7月17日以“民反”名义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胶州口共和大戏院(又名共舞台)召集全市各反日团体代表大会,以反对《淞沪停战协定》,每个代表胸前还佩挂一条红绸做的代表证,生怕别人不知道,结果遭到大围捕。共舞台事件导致88人被捕,其中13人牺牲。频繁举行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不顾实际、脱离群众,使党员干部成为行动的主要成员,这等于主动将同志送进监牢,而被捕者一旦有人叛变又引发新的组织危机。反动当局的镇压力度进一步加强,尽管宋庆龄和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发起成立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为之奔走呼号,尽管临时中央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号召援助世界职工运动革命领袖,8月19日牛兰仍被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无期徒刑。10月15日,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兴里11号住处被捕,同案系狱者多达10人。他们虽然都是被中共方面开除的托派成员,但仍在社会上激起一阵赤色党魁落网的喧嚣。
对临时中央安全造成更大威胁的是,国民党当局利用顾顺章叛变之机,日益改进增强的特务工作。这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筹办调查科上海行动区,加紧利用叛徒,安插内奸,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共青团组织原本就相对薄弱,首先遭到敌特的沉重打击。据1932年7月团刊披露,4个月来上海团部遭受大破坏计就有5次之多,由此波及到党的领导机关。9月,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的徐锡根被捕,曾为“六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工运界颇有名望的余飞在安徽安庆被捕。余飞竟将自己曾经追求的陈修良也出卖给国民党当局,当时陈修良正因起草不同意召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意见书而被组织停止工作,从安庆逃归的沙文汉前来报信,于是,赶紧转移。10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张文卿被捕,同月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袁炳辉被捕,继任者胡均鹤(陈炳和)不久也遭逮捕。
对步步临近的危险,临时中央不是没有警觉。早在淞沪抗战时,临时中央2月12日向共产国际发出组织报告,其中就提到“忽视秘密工作”问题。9月2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秘密工作问题,决定:“中央与省委在五日内必须离开旅馆建立房子”,“秘委应将如何与党内叛徒斗争与秘密工作的严重性问题在党报上发表”,秘密工作的基本条件应“重提到各机关讨论”。10月23日开会,决定将王云程加入中央常委,调史东(章汉夫)任省委书记,杨尚昆进中宣部。会上还议及加强共青团中央领导的问题,张闻天提出:“对CY中央的领导,还是邦(秦邦宪,引者注)去领导,我去是不适宜的”,“我对(江苏)省委的领导是不充分的,特别具体的方面,因为经验少,对上海不十分了解”,进而表示:“有人来时,我到苏区云,以学习工作”。两天后(10月25日),博古、张闻天、陈云开会。张闻天报告鄂豫皖、湘鄂西问题,总结鄂豫皖地区反“围剿”斗争的历史与教训,此时湘鄂西苏区已在强敌与内耗中凋零,残余力量只能突围另建新苏区。会上讨论常委分工问题,决定张闻天负责党报、宣传部、CY,并分管湘鄂西、赣东北、陕西。然而,会后没过一两天,张闻天所住爱文义路平和里27号团中央机关就被查抄,同居者被捕。有叛徒告密,张闻天侥幸得脱,在摩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的中央机关匿居了一个多月。
稍前,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已向共产国际提出将中共从上海迁至苏区的建议。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听取此建议,但暂未作出决定,只是要求“东方地区书记处和组织部应再一次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翌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婉地表达派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与张闻天去中央苏区的意见:“我们和你们的代表认为,为了帮助中央苏区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并清除那里的冲突,应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那里一段时间以督察他们的工作。伊思美洛夫和波戈列洛夫表示愿意前往。你们是否同意,请答复。”对上海危情显然未能感同身受的共产国际,10月27日如此复电“上海中央”:“请详细告知中央苏区的意见分歧。我们一无所知,因此不可能对派政治局委员去那里的事表示意见。”
这一天(10月2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分析敌情: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已遭破坏,红军被迫走鄂北,“但他并不能将我们主要力量受到损失”;“至于在湘鄂赣等方面,敌人是取守的形势。自我们采取进攻后,我们在黎川、建宁、泰宁等地已获得胜利。但决定胜负战争,尚在后面。可是我们可以断定,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张闻天还判断日本将占据北方的军事要点,不会有全国范围的军阀战争,并提醒“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只是空喊,没有切实去动员群众斗争”,他指出这回“左”的问题与过去的不同:“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易发生的,这一发生不是在于他们看不见个别先进群众积极性,而是在于掩盖其左倾消极。”10月29日,他又与会讨论了援助东北义勇军工作,会议还决定张闻天负责起草十月革命节15周年给苏联的贺电。此外,张闻天深居简出,将更多时间用于伏案写作。10月31日张闻天撰写《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3天后以“歌特”笔名在《斗争》第30期发表。“关门主义”这时期主要是用于批评赤色工会的工作,张闻天曾批评纱总的纲领是关门主义,后又自我检讨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厉害的关门主义”,这回张闻天借此剑指左翼文艺运动。文章批评左翼文艺杂志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明确:“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既而批评这种“左”的关门主义还“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想”,“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张闻天还卓有见识地指出:“在‘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决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者文艺的作品。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最后,他还纠正文艺大众化的偏颇,指出:“只有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图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观点,无疑的是错误的。”文章在结末部分憧憬道:“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
11月18日,张闻天撰文《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把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提到全党的前面,还没有充分了解到,宣传鼓动工作的转变,是转变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是使我们党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最主要条件之一。”张闻天写道,党的宣传工作堪忧:就在一个多月前,《斗争》刊物就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承认‘满洲国’”口号展开讨论,起因是有同志批评党组织4月间提出这一口号,认为是做了国民党的应声虫。当时党内同志就是如此之“左”,张闻天秉笔直书:“象目前我们所做的宣传鼓动工作,当然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批评宣传工作的形式限于传单、标语,倡导“利用图画,利用唱歌,利用戏剧等许多群众的宣传鼓动方法”,检讨没有充分利用左翼文艺家中的图画家、音乐家与戏剧家。随后,又批评:“在宣传鼓动的内容方面,我们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张闻天形象的称之为“‘党八股’(又名‘十八套’)”:“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他指出:“只有带有时间性、具体性的、适合于群众目前斗争的要求的宣传鼓动,才能把最大多数的群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的不同,团结在统一的战线之下。”张闻天斥责“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笼统武断,倡导“事实的证明与细心的解释”。他还批评“党八股式的宣传鼓动只能是秘密的与狭窄的”,指出:“虽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但是如若我们能够彻底的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那就可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公开可能没有利用,还有许多地方能够争取公开。”最后,张闻天还涉笔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联系,“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就是组织群众的工作。”
当此“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之际,临时中央仍牵挂苏区的反“围剿”。11月2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指示。中央电文第一句便是:“听了陈赓同志的报告”云云,陈赓是去年9月离开上海前往大别山的。电报指示:“现在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豫鄂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建立与中央的密切关系”。
上海环境更趋恶劣,11月建立的国民党中统系统的上海行动区总部加紧破坏活动。12月1日,沪西团区委开会时突遭包围,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团省委巡视委员会委员李干成、团区委书记阿肖(陈同),以及骆何民、关玉书(荷兰籍华人)等被捕。原来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员黎行叛变告密。在此前后被捕的一些曾在中央,在党、团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者(包括因参与反对派活动被开除的),叛变后发表自首书,一时浊流滔天。11月2日,余飞抛出《告共党同志书》。12月16日,袁炳辉、胡均鹤(陈炳和)与胡大海(程金芳)、陈亨洲(陈文远)联名的自首书登报。12月20日,《许畏三脱离共党,劝共党同志自首》书发表,许畏三还带便衣警察抓了张金保。12月31日,又有《前共产党中委徐锡根劝共产党员自新》见报。一些叛变者还甘当鹰犬,严重威胁到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安全,以及共产国际在沪的秘密工作。12月初,新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兼驻沪的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向共产国际如此报告所处险境:“经常进行搜捕,首先是在上海。最近两个月来,大约进行了200次逮捕,被捕者中有一些是省(党)委负责人。试图通过逮捕来瓦解企业中的支部。据说从南京派来了200多新密探。由于青年组织书记的叛变,试图寻找[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很大一部分被捕者往往被引渡给南京当局;在那里遭到拷打,部分转到敌人方面,更多的则被枪毙。”共产国际对外联络局驻上海代表格伯特12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进一步通报危情:“绝对有必要考虑一下在保存许多文件的房子里开会时进行武装抵抗的问题”,并提到袁炳辉、胡均鹤两任团省委书记被捕使5所秘密机关点暴露,远东局同志与黄平、李竹声分别会晤的两所房子也被监视起来,“几乎所有青年团领导同志都被捕了,而与我们有联系的党员同志遭到警察追捕,随时都可能被在这里积极工作的15名奸细出卖。”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在莫斯科的进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1月2日,王明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请求帮助解决“对于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三个问题,其三便是深关中共临时中央命运的“关于中共央的所在地问题”:“根据一般政治上的考虑和由于骇人听闻的恐怖,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因此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党在上海的机构并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的问题。”信末,王明嘱托:“请尽快将这些问题提交讨论并让斯大林同志参与解决这些问题。”12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专门听取有关中国问题的议题,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中国]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在上海只留下这些机构的全权代表。”并“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拟订给中共的必要指示。”
此重要指示传递也要化费时间,这时临时中央为领导成员的安全问题焦躁不安。12月5日,临时中央同埃韦特一起致电共产国际征求意见:“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引者注)处境很危险,因为到处都有搜捕他,其他领导同志也受到威胁。两种可能:一是派他去北平,那里他不出名,但他反对这样做。二是派他去中央……区,这他愿意。目前[去那里]的旅途上有危险。急复你们的意见。”
共产国际的决定终于来了。12月7日,临时中央给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心绪应当趋于平静。不过,书信仍以指陈问题为主,要求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加紧义勇军运动等。12月19日,临时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建议留一名中央代表、一名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和一名负责联络的同志在上海,“并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来领导整个联络、印刷、无线电和情报工作。”还通报中央留沪代表是李竹声,“并立即派赵容去你们那里作为我们的新代表。”电文还提到张闻天、秦邦宪、王云程和陈云逐渐地去中央苏区,并将派一名代表前往湖北,此人当是黄平。3天后(12月21日),共产国际草拟发向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核心的决定。”并对临时中央撤往中央苏区后“加强上海中心”提出具体指导意见,除了李竹声外,“建议利用不久前派去的不为警察侦探所熟悉的”的盛忠亮等人,埃韦特则“应留在上海帮助[中共]上海中央局。”
就在临时中央准备撤离的同时,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临时中央决定缩小党组织,恢复各级组织的严密领导,实行单线联系。胡均鹤等人的叛变,直接威胁到主管群众工作的陈云。党组织要通知陈云,但不知陈的住处。正准备前往中央苏区的杨尚昆已中断了在上海的一切联系,直等秘密交通安排起程,突然有同志来找他,问有无办法向陈云报警。杨尚昆做救济失业工人工作时,知道陈云这位领导同志的住址,便说:“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现在是否还住在那里不敢说。我可以闯一下。”于是,就冒着瓢泼的冬雨,雇了一辆黄包车,放下车前的挡雨帘,从静安寺路梅园新村赶往北四川路。到目的地后,杨尚昆小心观察:弄堂口有无黑色的警车,周围有没有暗探在审视来往行人,再看报警的暗号动了没有?发现一切正常,这才鼓起勇气去敲门。陈云没有回来,来开门的与陈云扮假夫妻的陶恒芙,是心病专家陶恒乐的姐姐。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杨尚昆匆匆写了一个字条,托陶务必转交陈云本人。
因此得以安全转移的陈云,12月23日深夜11时许,遵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特科具体安排下,乘坐黄包车来到北四川路一路电车掉头处。下车,将头戴的铜盆帽压低眉梢,一件从吴淞路淘来的旧西装大衣领头翻起掩住两颊,陈云四顾见无人盯梢,便快步走向沿街一座三层楼住宅的门前,见门上有预先告知的记号,于是,轻扣两下。女主人出来应门了。“周先生在家吗?我是某先生要我来的,要与某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很客气地请进,上楼。瞿秋白早将一切准备好了,几篇稿子、几本书都放在杨之华的包袱里,另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衣服,“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瞿秋白对陈云说道,并问:“远不远?”“很远,”陈云转身就要下楼去叫3辆黄包车,却被男主人劝住:“不用你去”,他招呼女主人去办。这时,瞿秋白回过神来:“你们会过吗?”“没有。”陈云、男主人同时回答。秋白郑重介绍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久仰得很。”陈云真心实意地说道。

鲁迅
瞿秋白临别时还与鲁迅相约,自己要的那两本书,想请鲁迅过几天交陈云转交。然而,陈云最终未能如约再访鲁迅。形势实在太险恶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卢福坦被捕,随后变节;黄平12月14日在天津被捕。

瞿秋白
走,赶紧撤离。
事实上,相应撤离工作早就启动,11月间就转移了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李富春、蔡畅对蔡母隐瞒了蔡和森去年赴港后因顾顺章的出卖被捕,受尽酷刑后遭枪杀牺牲的消息,忍着巨大的悲痛,他俩离沪前往瑞金。12月,张闻天匆匆离沪,没有去看望父母一眼,虽然知道其父那年在上海《新闻报》登出启事:“母病危,盼见儿,速归”。刘少奇挥别妻子何宝珍还有自己的儿子,前往中央苏区。想到任弼时离沪后,陈琮英被捕,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一同坐监牢,刘少奇对家属实在是割舍不下。
与此同时,还有同志不断地来到上海,找党组织,找中共中央。1931年秋被派往湘鄂西苏区的谢觉哉,经历在洪湖地区被白军俘获的劫难,逃到上海。湘鄂西苏区被夏曦这帮极“左”派肃反加冒险给弄丢了,周逸群在自己到苏区前就光荣牺牲,算是死得其所,柳直荀、段德昌、李剑如这样的好同志竟被自己人错杀,天理何在!在中共六大后调至上海在江苏省委和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阮啸仙,一度赴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1年9月因北方局遭受大破坏而回沪,这年冬调任中央互济总会援救部部长。12月受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中央执行局中共党团书记。此时新任的全国互济总会书记是邓中夏,他回沪后长时间受到冷落,后任沪东区委宣传部长,其妻李小妹(化名李英)再三请求组织把他俩调在一起工作,就在10来天前李小妹被捕了。革命者亟需互济,只是互济会因受“左”倾错误政策干预,盲目斗争,脱离群众,接连遭受严重破坏,其实自己也走到了悬崖的边缘。1932年底,由苏联回国的林伯渠面对的就是如此肃杀异常的上海。
1932年的最后一天,临时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华北给河北省委发去指示信。两天前(12月29日),时在联华影业公司从业的共青团员聂耳在日记中记道:“《三个摩登女性》受了好几次的检查,结果修改了几个字幕通过了,今天已公映。”该片系田汉编剧,音乐表演场景由聂耳参与导演拍摄,实为大半年前瞿秋白拍板夏衍等左翼作家进军电影界所飞来的左翼电影第一燕。对此内幕,党内同志虽大多不了解,但是电影界在淞沪抗战后的新气象还是有所感觉,无闲情进电影院,也能看到左翼影评。
艰难地迈入1933年。元旦日《东方杂志》推出新年号,刊发142位全国各界人士对未来中国、对个人生活的梦想。“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一个大联邦。”时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直言胸臆,“而我们的中国呢,当然也是这大联邦内的一个部份”。女作家谢冰莹、神州国光社编辑胡秋原也写下此类憧憬。一名失业三年的普通读者毫不讳言地说:自己要“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30年代上海大潮澎湃。
1月2日或3日,杨尚昆奉命住进法租界的一个旅馆。临时中央原指令杨尚昆在张闻天走后接任中央宣传部长,后又拟派往顺直、满洲,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去中央苏区。不一会,来了两位秘密交通员,接上关系后,来者打开小箱子,取出事先购置的衣服,让杨改装。当晚,交通员就陪杨尚昆上船,开启前往瑞金的旅程。
黄平被捕后触电自杀未遂,随后叛变。他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上海的中央机关则只吐露了政治局开会的地点,至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均只字未提。就是这样,当黄平所写的《自首书》刊登出来,还是激增了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危机。临时中央加紧撤离党员骨干,陈潭秋正是在年初接中央决定,准备偕其妻徐全直去中央苏区的。1月7日发出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和进攻华北告全国民众书》,成为临时中央最后产生的文件。1月16日,共产国际就筹办远东反战大会致电中共中央并抄送共产国际代表,临时中央实已无法应承,只能交付留守者。
1933年1月17日,黑色星期二,农历癸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一天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明确中国工农红军“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众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宣言历史性地突破了以前“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透显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重大调整的努力。这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2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起草的,临时中央至多仅是“二传手”。
也正是在这一天(1月17日),博古告别怀孕在身的妻子刘群先,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
走得实在匆促,去年临时中央10月决议来年1月18为“全国的失业运动日”,没想到都等不到这一天。大量中央机关包括秘写处、油印处、无线电台,以及中央特科、交通站、济难会、出版处等,连同建党以来的大量文件都留在了上海,两三千名共产党员留在了上海,还有400多人的左翼文化组织及其中央领导瞿秋白。上海的斗争还要继续,这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劳苦大众,还有不断涌现的热血青年,“社联”同志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将论敌打得一败涂地,马克思主义还是闪耀着真理力量的光芒。受这场论战的影响,茅盾1931年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子夜》,其间受到瞿秋白的指教,1932年夏部分章节发表,全书于1933年1月震撼问世。小说描绘了中国农村破产、世界经济危机、金融买办投机肆虐的众生相,凸显了民族资本在多重挤压下加紧压榨工人、激化劳资矛盾的残酷现实,形象地宣告了实业资本在中国穷途末路的宿命。其中女共产党员玛金的艺术形象,是以当年在上海从事女工运动的金维映(人称阿金)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多次写到玛金那“尖利而精神饱满的眼睛”,她因抵拒“左”倾错误而被指为右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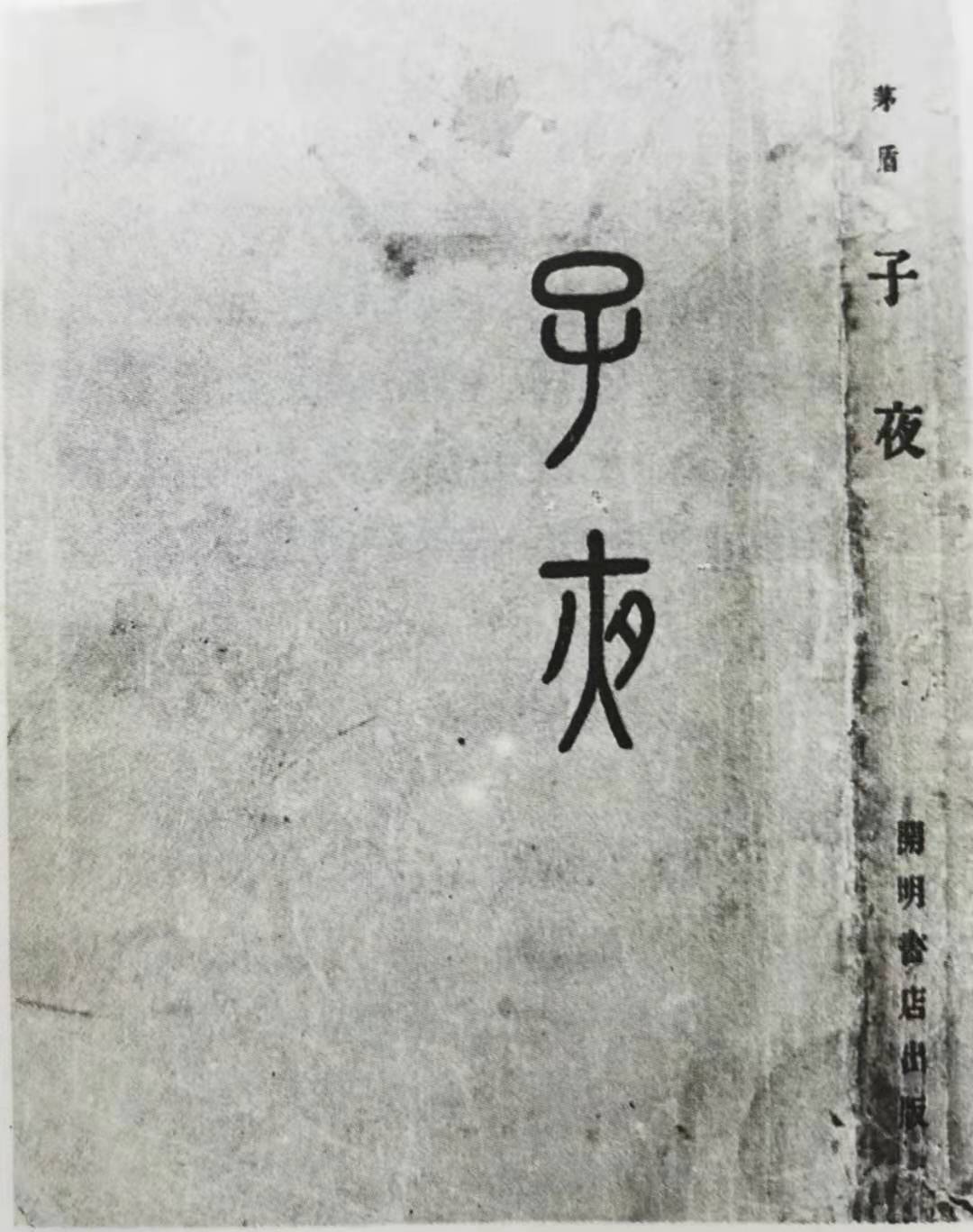
《子夜》
子夜,这正是中国革命长夜难眠、转机暗伏的时分。

 吴海勇,文学博士,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参与编撰党史集体成果十数本,发表个人署名论文、文章逾 200篇;个人著述出版有《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决绝态度》《列兵毛泽东》《“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等十数种。
吴海勇,文学博士,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参与编撰党史集体成果十数本,发表个人署名论文、文章逾 200篇;个人著述出版有《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决绝态度》《列兵毛泽东》《“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等十数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