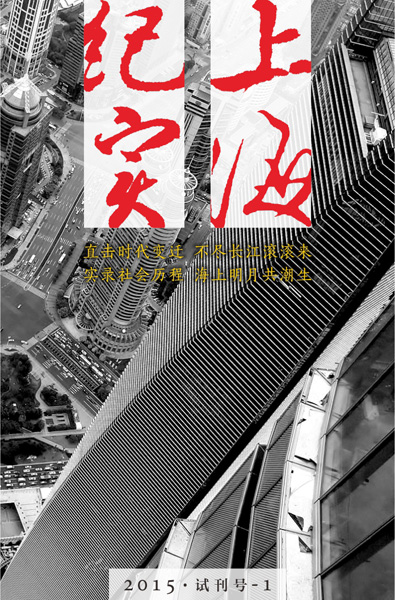常听一些年轻朋友说,这是一个大家都忙着“刷存在感”的时代。也不知他们说的“存在感”到底涵纳了哪些人生况味,其中是否包括尼采所言“给生成打上存在的烙印”之义。但无论如何,热衷往往意味着缺失,如果这真是一个大家都忙着“刷存在感”的时代,那么很有可能,这也是一个大家普遍缺乏“存在感”的时代。
真希望这只是一种随便说说,而非辽阔且坚硬的“事实”。可是转念细思,今天又确实有太多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存在价值产生怀疑,大家无比“现实”和“真实”地活着,同时感到蚀骨销魂般的“虚假”和“虚无”。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在自我与他人、社会乃至全世界之间重建一种真正的、有意义的关联,以期获得人生中新的“真实性”和“现实感”。
在文学场域,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纪实写作的复兴(非简单复活,乃继往开来),也或多或少指向了对那些“真实的虚假生活”(包括人们相应的阅读和写作行动在内)的不满和反抗。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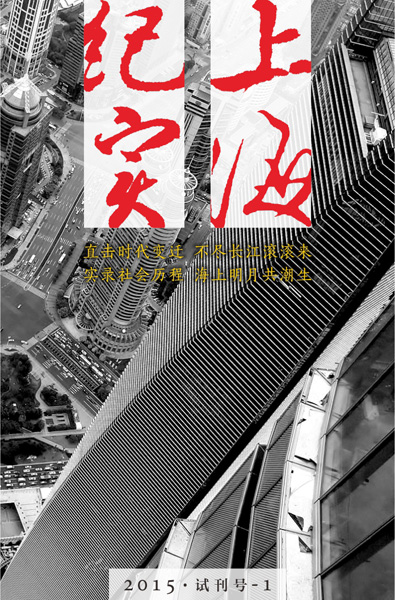
现如今是个“消息过度”的时代,人们在受到海量消息碾压的同时,又对种种消息乃至新闻的信度产生极大怀疑,更糟糕的事情在于,每每当这怀疑尚未有结果之时,蜂拥而至的新消息和新“热点”便已将“过去”无情淹没,众人也因此被无情地裹挟而去。例如,“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一事在今年春节期间可谓赚足了眼球,全国网民站队声讨,以各种方式“怒刷存在感”。按理说,这个本可以成就一次全民介入公共讨论空间,进行观念交织和思想碰撞的媒体事件,最终却被认定为假新闻,从而使公众理性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备受打击。再如“天价鱼”等其他公共新闻事件,在某些不良媒体的刻意引导下,转变为一波三折的戏剧故事,致使事件背后的真相迟迟不被发掘。所有这些,一旦“热点”冷去,便通通不了了之和恍若隔世。那本被众人预约于“怒刷”中的“存在感”,自然也在各种各样的匆忙和仓皇间无从追寻。更大的问题在于,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这种不断被生产出来的“不了了之”和“恍若隔世”,都将在我们体内蓄积愈来愈深的不真实感和“虚无感”。
笔者认为,现在人们对非虚构或纪实文学的热情,必定有一部分可被溯源至此。换言之,非虚构或纪实行动的对峙点不在“虚构”,而在“虚无”。人们不仅憎恶于虚假的新闻和消息,而且在新闻和消息固有的“快”与“点到为止”之外,开始倾心于种种必要的“慢”,开始著力于一个点一个点地“深挖”、“深耕”和“深描”。而在这“慢”、“深挖”、“深耕”和“深描”的背后,则是大家对那些与自我、他人、社会、世界息息相关的不可靠、不彻底、不深情的厌倦和反动,同时也是大家想要让某些人生世事走进心里、长到肉里进而持久“存在”的真切渴望。
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刊物《上海纪实》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就其已经面世的三期内容看,这份刊物正试图建设一条让大家奔赴持久“在场”的文学道路,也试图使自身成为一个真正朝向“真实性”和“存在感”的文学空间。“《上海纪实》倡导‘在场’精神,关注当下,直击现实,记录历史和时代变迁,反映社会进步和人的精神成长历程,体现创作者的责任担当、理性良知和人文情怀,追求真实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三者统一。”朱大建在“主编的话”中所说的这一句,实属雄心勃勃、旗帜显豁之语。笔者看到,《上海纪实》前三期杂志每期都设有“在场、亲历、经典、万象、记忆、往事、微记录”等栏目,并刊登了《道路清扫工的一天》《“小联合国”秘书长》《火灾调查专家神秘故事》《上海全职太太生活面面观》《<小木屋>(选摘)》《与黄宗英争议<小木屋>》《<傅雷与傅聪>创作手记》《在“世界中心”遇见“我”——冈仁波齐转山行记》《上海“猎狐”风暴》《山高人为峰——“上海中心”建造纪实》等“新”人耳目的作品,一时间宏微并举、幽明俱呈,既映照了世间万象,书写了平凡人间,又不曾躲避对重大事件的及时聚焦和对英模人物的必要传写,而且多数文章也都能有意识地贴着现实、贴着他人和自我的真实走,并未预设什么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穹顶。
其中,不少作品以“在场”化或“亲历”性的纪实笔法对具体人事进行呈现,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又应有人知的“现实”,如“火灾调查专家”谢福根、“警界杨子荣”葛国勇的特殊工作,如“上海中心”的建造过程和技术难题,这些作品都让开了传统报告文学“突出先进人物、彰显雄厚国力”的写法,合理克制了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冲动,乃是殊为可贵的尝试。
在“经典”栏目中,《上海纪实》每期回顾一位优秀纪实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令笔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第一期对经典之作《小木屋》部分内容的重新刊载,以及罗达成的《与黄宗英争议<小木屋>》和陆正伟的《不落征帆的黄宗英》两篇文章。“都说报告文学不是用手写出来的,首先是用脚跑出来的”(罗达成语),遥念当年黄宗英为采访和传写研究高原生态保护的女科学家徐凤翔,出行前竟给亲友留下遗书,“舍身跑入”西藏腹地进行“在场”式考察和访谈,实在是老一辈报告文学作家秉持崇高的写作伦理和职业精神的极佳体现。如今,大家在新的生态视野和现实语境中相互对话和对接,把事关所有人的生态大事再次凸显出来,可谓既是对我们前面所说的“深耕”和“深描”之典范文本的温故,又是对全球生态危机这一压迫性事实的回应。全可被视作是一种对“深耕”的“深耕”,以及对“深描”的“深描”。
这些,足可展示出《上海纪实》作为一份刊物的敏感和抱负。
二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国内发展势头迅猛,影响亦非同寻常,从《上海纪实》前三期当中,我们也能明显觉察到积极的呼应。就其刊发的一些文本而言,第一期的《我和父亲之间》、《道路清扫工的一天》,第二期的《父亲》、《“我觉得上海就是故乡”——初中同学华子自述》,第三期的《在“世界中心”遇见“我”——冈仁波齐转山行记》等,就和当下的种种非虚构写作很难区分开来。例如《“我觉得上海就是故乡”》一文,是以访谈形式呈现了“华子”近年来的生活状态,其中还包含了我(王磊光)与华子的一些共同情感体验。从文本的实际效果来看,它既显得比新闻更具情感温度和文学色彩,又比虚构文学更具现实感。再如《道路清扫工的一天》一文,则将关注点放置在那些极易被世界忽视的平凡小人物身上,从幽微的细节入手,展现出一个族群的生命状态和喜乐悲欢。
但不能不提的是,《上海纪实》自我定位乃“刊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电子刊”。此处抽象而论,传统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往往指向宏大叙事,热衷于书写大事件和中心人物,与主流价值观贴合密切,徐成淼在对比分析后就指出:“其一,传统的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常常具有强劲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对事件的正面描写和全景式扫描,强调人物的英雄式塑造,而当前的‘非虚构’文学则舍弃对重大事件的正面叙述,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遭遇与个体感受;其二,传统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有着太多的‘虚构’成分,而当前的‘非虚构’文学则大力排斥虚构,多以作者‘现身说法’和当事人“口述实录”的方式把事件的原生状貌尽可能真实地呈示给读者;其三,传统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受古典形态文学的影响很深,其结构方式、叙述方式和语言形态基本上是古典的,而当前的‘非虚构’文学则在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上更趋近于现代形态,它那种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距离的内在质地和外观姿态更切近现代人的自由心情。”(参见龚举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如果放在更为远大的时空中观之,我们实际并不能截然评判和认定哪一类创作取向和路径更具合理性,我们只能说,无论是起于“庙堂”还是发自“民间”,在理想意义上,写作者们都可以为时代进行有效的“纪实”和“表情”。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被生产出来的文本是否真正地朝向了“事实”与“真实”,是否真的做到了“实事求是”,同时又具有广大读者愿意接纳它们的时代语境和氛围。
也许更为可行的做法是:无论哪一类创作,都能够不断尝试突破与融合,而非偏执地固守其城。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曾言:“经常有人说,我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地快。内容打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边界:音乐、绘画,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我的老师阿莱斯·阿达莫维奇——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是对20世纪那些噩梦的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因此,纪实也好,非虚构也罢,其实都没有必要强持于所谓集体/个人、虚构/非虚构、古典/现代等等的硬性划分,而更应该经由各种富有创造性的行动,在作者、读者、媒体和世界之间建立更加可靠且更有力量的现实关联,进而让大家在过写作与阅读的生活时,能拥有足以祛除内心空洞与虚无的“存在感”。
如此说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既是“纪实文学”胜利,或者“非虚构写作”的胜利,更是一种写作者进行突破、越界与融合的胜利。而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倡导的“超文学”,实属于一种将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新闻等不同叙述方式汇聚一川的创造性文体,这种创造性将使写作者打破各种旧有的边界陈规,通过不断的越界行动,去抵达纪实写作所能抵达的更远境地。
三

显然,《上海纪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越界与融合”的必要性,并且由里到外进行了自己的种种创新。其中最外在的,无疑是刊物在作品登载形式上的媒介融合策略。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大家书写与阅读的“生态环境”,《上海纪实》审时度势,首先以电子刊物的形式面向读者,即在上海市作协主办的“华语文学网”和“上海纪实”微信公众号进行双版本发行,从而使一些独具特色的纪实文本同全新的传播载体相契合,呈现出“互联网+文学”的全新样貌。这种新的尝试不仅使得刊物内容得以更好的传播,还可以突破纸媒的限度,增加新媒体独有的优势。比如“微视觉”栏目中的音频、视频作品,无疑会让刊物内容显得更加新鲜、立体。
当然形式创新之时,内容突破依然是重心所在。在这方面,国内外创意写作的蓬勃发展可以提供不少有益的参照,比如该领域的核心理念是倡导“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每个人都有创作的潜能”,这是一种极具革命性和民主意识的书写理念,它对以往那种文学创作只能被少数人垄断的特权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柯翌嘉因此认为,这种“写作权利的下移”绝对是一块值得不断挖掘的宝藏,笔者也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上海纪实》有必要留意从民间拓展作者资源,譬如不断去发现、培养和推出像姜淑梅(著有《乱时候,穷时候》等)和秀英奶奶(著有《胡麻的天空》)这样的民间写作者,两位正在写作中继续“奔跑”的奶奶级作家都是“草根”身份,而且都是在年逾花甲之时才开始认字读书,却是一出手便显得身手不凡,这一现象实在值得关注与思考。
除了拓展民间作者资源,未来的《上海纪实》亦可著力于来稿选题和文本呈现上的“创意优先权”。既然新媒体刊物可以为图文作品和视频、音频类作品提供十分便捷的平台,那么相对于传统纸媒,《上海纪实》在选题上就已经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资深图片编辑马宏杰的《最后的耍猴人》一书,就以跟拍耍猴人12年之久所收获到的体贴认知和幽微观察为底色,将深度写实的摄影作品和客观平静的文字叙述匹配一处,生产出了一种冷暖交织、悲喜同在的文本效果。在《最后的耍猴人》之前,马宏杰还著有《西部招妻》,之后又出版了《中国人的家当》,作为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和写作者,马宏杰曾感慨说,中国大地上的百姓故事实在是太丰盛了,好的选题简直多得做不过来。而马宏杰所言的这类选题及其所取的多媒体文本呈现形式,全都跟《上海纪实》自身的平台特点非常相契,十分值得开掘。再比如国内第一本原创自然笔记类著作《自然笔记——开启奇妙的自然探索之旅》,则是“将原本即是图文一体的自然笔记手绘作品和文字故事相结合,用一种平凡人间零距离交流的简单质朴招呼大家一同去亲近自然和记录自然”。(参见笔者所撰《非虚构写作的“特权”与“创意”》一文,载于《雨花》2016年第1期)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回归自然的怀抱,包括从阅读上回归一切撩人心弦的自然书写。而自然笔记正以其独特的性质与功能绽放了一种双重耕耘与收获,它既书写生态,又创造生态——前者指向符号化的写作与阅读,后者指向现实性的生活与实践,可谓将人们的个性化自然书写、心灵环保与绿色多元的日常生态建构一体化、家园化了。因此既有广阔的读者市场,如城市居民的绿色阅读需求与国民教育中的自然教育需求等,又符合未来生态伦理需要,可以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力量。(参见笔者所撰《中国大陆自然笔记的兴起——对一种创意写作新文类的近距离考察》一文,载于《雨花》2015年第3期)而目前来看,上海地区的自然笔记创作又在全国尚且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也大可为《上海纪实》在生态文学作品方面的选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只要能始终秉持真诚,真正去刺入现实,反抗虚无,且勇于创新与融合,拥抱创意,相信在未来的生长中,《上海纪实》一定能够借助上海的地域优势和各种文化资源,在“互联网+文学”的时代里打造出一种属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的新传奇。
(原载文学报)

 吕永林(左),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创意写作教研工作。
信世杰(右),山东滨州人,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硕士,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活动。
吕永林(左),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创意写作教研工作。
信世杰(右),山东滨州人,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硕士,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