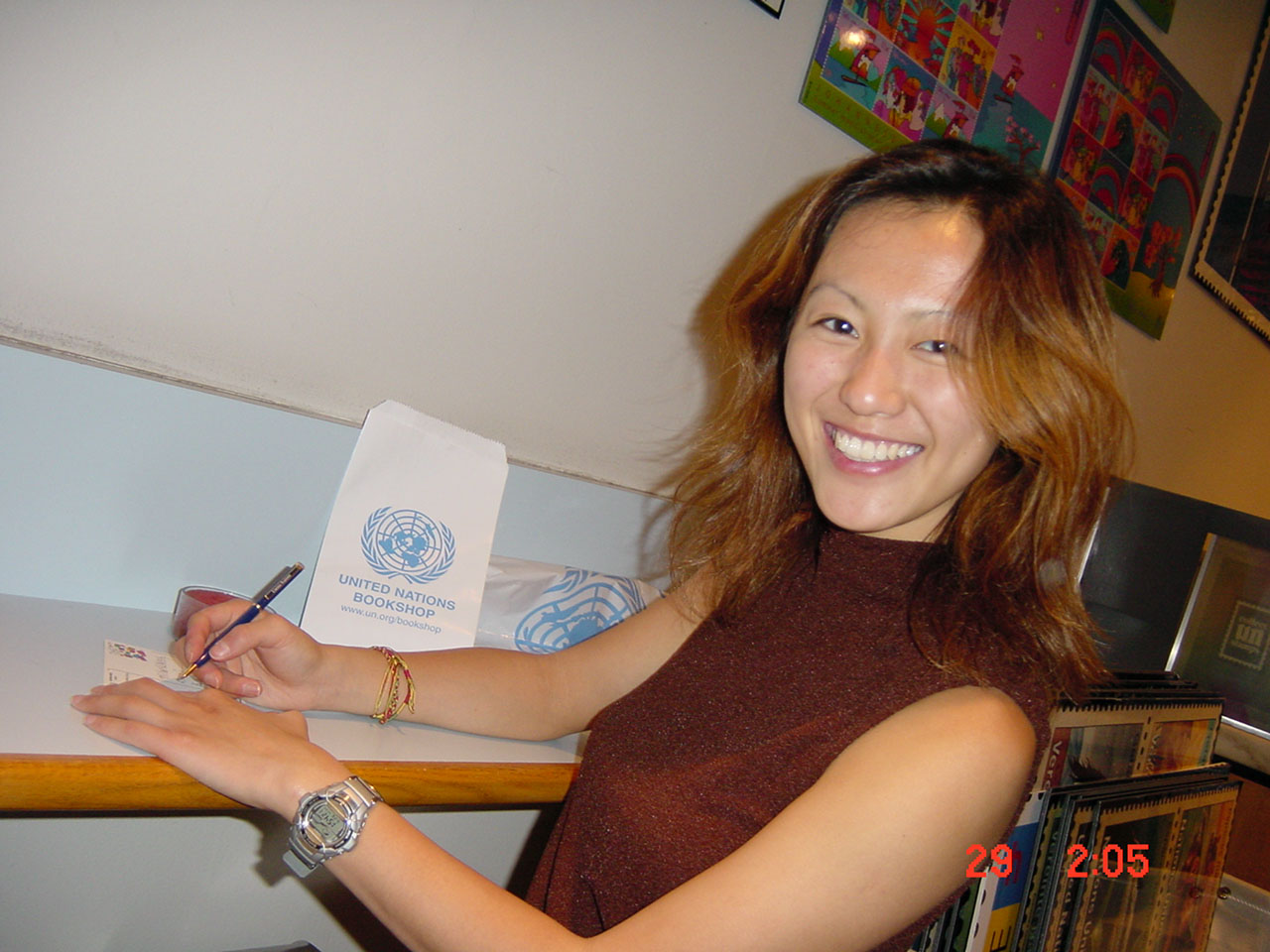弹指之间,我在美国生活的年头已经超过在上海长大的年头了。回想在异乡的这19年,就像童年的记忆,并不是连续的,最快乐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刻记忆犹新,大多数的日子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

离开
还记得离家去机场的那天,我去奶奶家敲门告别,奶奶不愿意开门,隔着门叮嘱我要小心照顾自己。终于爷爷打开门,我看到奶奶泪如雨下,爷爷挥挥手,叫我赶紧走吧。离开家后的这19年里,每年会回家,每次2-3个星期,可是正如人所说,当你一旦离开,你就再也回不来了。还记得当我从美领馆拿到签证后,兴冲冲地回家告诉奶奶,奶奶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吓了一跳,奶奶一直是“大人”,大人是不哭的。走那天,蛮多人去机场送我,我完全不知如何应对告别的泪水,拖着我的行李箱匆匆逃进了登机口。多年后,我听到爸爸对别人说,“这小孩头都不回,拖着箱子就走了”。其实我也是泪水满面,只是不敢回头。还记得那年我被同济录取,拖到最后一天晚上骑车去学校报到。骑了蛮远,我回头,看到路灯下爸妈黑色的身影依然在那里。我不知他们在夜幕中有没有看到我不舍的回望。我自己亲爱的女儿刚刚5岁,我已经可以想象若干年后目送她远去的背影。一走,一送,我的心有着同样的离愁。
留学
爸妈花尽心思给我找了市场上最大的硬盖行李箱,还是粉红色的,目的是我可以多放一点东西,在机场的行李带上好找。结果,那箱子太重了,我使尽吃奶的力气把它拖下行李带的时候,一下砸在地上,还没出机场就摔破了。从那一刻起,我他乡留学的生涯就开始了。学校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叫里士满,从芝加哥要转机乘一个20人的小飞机再飞1个小时,再从那个小机场开车45分钟才到学校。刚到学校的第一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用洗衣机,决定用肥皂手洗几件贴身衣服。太累了也不知道肥皂在箱子哪个角落,在厕所的洗手台上看到一块黄黄的东西,闻上去蛮香的,拿来就洗吧。怎么洗也没有泡沫,我想这美国的肥皂怎么这么奇怪。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肥皂,是熏香用的!
在学校的日子是美好的。学校很小,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1200个学生有大概50个国际学生。我们国际学生之间关系很好,常常在一起做饭,聊天。每周礼拜四晚上是我和我的法国室友固定的电视晚。我们寝室里没有电视,每个宿舍楼地下室有一台电视。我们会点一个大比萨饼,买一罐巧克力冰淇淋,连着看好几集我们喜欢的电视连续剧。回想那时真是能吃,这么多东西,每次吃得精光! 闲的没事做的时候,我们会几个人开一辆破车,去兜风。印第安那一片平地,一眼望去全是玉米地,我们的车就在比人高的玉米地里漫无目的地开,窗户摇下,现在还记得那时间仿佛凝固的景色和暖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到了冬天,大雪纷飞,风吹过去,一团团雪花从地上卷起来,一眼望去,一片无边无际的白。我当时想,南极也不过这样吧!老师和同学对我很好,从来没有让我觉得不受欢迎,或者不自在。倒是我因为不很了解情况,有些自我封闭。现在想想,如果是现在的我再重新过次四年的大学生涯,我会更投入,感受也许比现在更深。离开学校后,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会去学校的网页看看,总让我觉得浑身暖暖的。
刚开始的时候英语是个问题。所以我只跟国际学生在一起,大家都有口音,因此,我没有自卑感。我还记得,第一个寒假我没有回家,为了个现在想想很蠢的理由: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离开家时间的纪录!我因为学期里在英语系里打工,认识了一个英语系的教授Lincoln。Lincoln寒假要去度假,就叫我住他家,帮他们照顾他家养的猫。我还记得晚上,我就会看一段英文的书,然后让自己大声再把这一段内容用自己的话(英文)重新讲一遍。因为我认识到,听不是问题,讲和表达难多了。在大学读1,2年后,我的美国同学都听不出我有任何口音。

当然会想家。1998年7月离开家,直到1999年12月才第一次回家。1998年12月元旦前夜,里士满大雪纷飞。我一个人在Lincoln家的一大幢房子里过了3个星期。其实也没有太难过,只是会想,爸妈此时在家干嘛呢?想着想着,就跑到前院,用脚印在厚厚的积雪里踩下了“新年快乐”四个字,搬了把椅子,爬到椅子上,把字拍了下来。回到房子里,放上一卷Dixie Chicks的磁带,写了一封信给家里。直到现在,我还可以记得当时的桌子,当时的音乐,当时在路灯下莹莹发亮的白雪。离家后第一次回家那天快要到来前那几个礼拜,是我这辈子记得最兴奋的几个礼拜。我不停的想象机场里爸爸妈妈来接我的景象。我想象自己扔下行李,远远地就跑过去,拥抱我的爸妈。
在大学的第一学期我从49公斤膨胀到59公斤。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如何均衡自己的营养,每天在学校的食堂就光吃喜欢的东西。一天三顿,好像有两顿以冰淇淋结束。室友拖我去参加学校的网球队。网球,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很喜欢,经常随便找人打打,可是没有进过专门训练。虽然我担心出丑,可是想到可以打网球就去了。第一天训练一开始就是跑步。以前在学校想到跑800米就腿发软的我,赶着鸭子上阵了。跑了大概几百米就不行了,我问这是要跑多少啊?队友们说3英里,我脑袋一转:天啊5000米!实在没办法,我躲在教练看不到的地方,等到她们一大圈跑回来,再次加入装模作样地跑回去。从那天起,我开始每天跑步。我不能让自己失败。直到今天,每天只要我有时间,我还是会跑20-30分钟。我还记得好不容易拿到第一份工作的招聘合同时,我高兴得换上球鞋跑了很久,一边跑,耳朵里全是自己砰砰的心跳声。
大三的秋季学期,我去了德国和奥地利游学。上海格致中学毕业后,我在同济大学学了一年德语。从那以后,对德国始终有些好奇有些向往。在尔汉大学修了一个德语的副学位,并很兴奋地报名参加了为期一个学期的游学。学期开学的第一天,要求我们大家在德国一个小城市马尔堡会师。我那年暑假没有回家,在学校帮英语教授照顾猫和计算机系里打工。我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旅行介绍书LONELY PLANET, 每天下午跑完步就坐在后院的露台上,看着那本书,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欧洲之旅。
终于,启程的那天到了。先乘坐一架20个人的小飞机从离学校40分钟的代顿机场飞1个小时到芝加哥。再转机从芝加哥抵达法兰克福。最后那一段从法兰克福到马尔堡的路程要坐火车。在我的脑海里,对火车站的理解来自于我14岁那年第一次自己和几个同学从上海去北京玩的时候坐火车的经验。只记得,要早点到火车站。火车会在站台上等乘客,那一系列候车,验票,上车的过程是个浩大的工程。于是,我早了20分钟到了法兰克福车站,刚找到对的站台,火车就开过来了。我想也没想就上了车。我前脚刚上车,火车后脚就关门开动了。我一边啧啧称赞这德国名副其实的高效率,一边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火车飞驰了一会儿,接下来停靠的车站不在我的行程表上。车厢里的喇叭报着站,我集中起全身的注意力,就是没有听到马尔堡。脑袋里像被轰炸机炸过一下,几分钟后,检票员过来了。我挤出了平生第一句说给德国人听的的德语:我要去马尔堡。接下来的几分钟,无数德语从我耳边飞过,检票员对我讲话,在我表示完全不明白后,跟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开起了大会。我只觉得无数的眼睛在看我,世界完全在我掌控之外旋转。终于,检票员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转车的路线,我拖着好几个箱子,换了几条火车线,终于和大部队集合了。
那半年,行李箱就是家,我晚上做梦都是在站台上等火车。去了德国和奥地利很多不同的城市,在很多不同人家里寄宿。在东德莱比锡的一个博物馆里,东德过去的生活被陈列在玻璃框里,那时的电视节目,音乐,小朋友带红领巾的方式,他们敬礼的方式!我惊讶无比地看着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被展示在一个个玻璃框后。后来回头看看,这几个月对我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影响。这几个月的“度假”,我没有平时的常规,没有平时必须完成的作业,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文化每天挑战我熟悉的默认的习惯准则。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世界之大,我们彼此的文化可以如此不同,可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一样的。我们都那么不一样,接受自己和别人的不同,接受别人和自己的不同,包容彼此让我们更强大。
工作
转眼就到了大三,找工作的事成了我整个生命中唯一的主题。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是很关键的实习期。我投了很多简历,终于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让我飞去纽约参加面试。我还记得自己反复研究参加面试的邀请函,什么消费是可以报销的,好新奇好开心!到了纽约住进公司安排的酒店,里里外外检查房间里有的设备,觉得真是好玩!到了晚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觉得怎么那么吵呀。虽然在繁华的上海长大,安静的里士满让我的耳朵那个晚上怎么也接受不了城市的喧哗。第二天,我穿上自己认为最体面的衬衫,也就是我所有衣服里唯一的一件有领子的衣服,走进了公司的大门。电梯一打开,我满眼看到的是笔挺的西装和短裙。当时脑子里就一炸,完了!整整一天的面试还是坚持过去了。一点都不记得任何面试官或者问题,只记得到最后被拒绝的时候,有多么灰心丧气。
回到学校,继续不停地投简历。整个暑假,没有一点回音。我每天来回于教室,图书馆,寝室,肩上觉得越来越沉。脑海里不停地闪过一句话:有一份工作对一个人的幸福感至关重要。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又是一个招聘季。终于美林证券打电话给我,要做电话面试。电话面试结束的时候,考官就邀请我去纽约面试。我这次学乖了,买了崭新的西装,坐上了去纽约的飞机。面试感觉不错,飞机离开纽约回印第安纳的时候,我从飞机的窗户里看到了猎户星座,每颗星都那么亮。印第安纳很平,我经常在晚上躺在草地上认星座。那晚在飞机里看到的猎户星座,仿佛就在我身边,伸手可触。
回来没多久,就收到了美林的录取通知。我无比高兴地绕着学校跑了很久很久。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也就是些衣服和一床被子,一股脑的塞进自己二手的Toyota Tercel的后座,就开车离开了亲爱的里士满,一直开了11小时,直达纽约。离开那天,我去和lincoln教授告别。他从小在土耳其长大,土耳其的传统里,在送别时,要给远行的人泼水,祝他们的旅程像水一样平顺。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他和他的妻子,为我泼水,我的眼睛湿润了。
那年夏天,我开始了在美林证券的第一份工作。从上海去到荒郊野外的印第安纳,是我自己的选择。高中毕业的时候,只想离开城市,离开人群。在乡下待了两年后,去柏林做交换学生一学期,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的还是城市的血。所以那时候申请的工作全部在纽约。结果呢?美林的那份工作还是不在纽约,而在一河之隔的新泽西。辗转反侧地终于找到一个在纽约的岗位,把自己搬回了向往已久的纽约。2005年美国房地产热火朝天的时候,发现自己对房屋贷款的债券化很有兴趣。这债券到底是怎么从无到有的呢?通讯录翻了又翻,问了很多朋友,终于找到了美林做房贷债券化的部门。面试,等待,好几个月后才终于如愿以偿开始自己第一次很想要做的工作。这时候已经是开始工作的第三年了。债券化的工作从2005年做到2007年。倒不是因为金融风暴, 是我自己不想再做了,因为觉得无聊了。这个工作每天早上9点开始,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每周基本一个通宵,其他几天平均是凌晨2点离开。我把家搬到公司边上,这样可以直接走路回家。那两年,晚上垃圾车几点出来收垃圾,早上4点半左右哪个卖早餐的开始出来设摊,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学,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并没有觉得怎么累。还记得刚开始独立操作的第一件单,已经半夜三点了还在算来算去,不管我如何费劲,就是还差几分钱,不知道在债券结构上出了什么错。那个单必须在早上6点前做完,早上7点楼下交易台一上班,就要用我的材料上市销售。那时刻压力好大。自己对自己说绝不能放弃,也绝不能失败。大半夜地出去走了一圈,清了清头脑,又回来把所有东西从头又做了一遍,终于发现了那个很小的差错。可是无论差错多小,只要一分不对,就不能上市。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挑战性,我做得津津有味。两年后,当一切都很熟悉后,我慢慢不能接受每晚待到凌晨2至3点。再加上长期睡眠不足,我仅有的空闲时间都在补觉,我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懒得搭理的人。赚的钱对一个20几岁的人来说,算很多了。我逐渐发现自己老觉得谁都没有资格告诉我该怎么做,即使是我不对。我老觉得自己赚足够多钱,工作这么幸苦,连睡觉都还来不及,别人谁也没资格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的世界里容不下别人。我决定离开这个工作。
正巧楼下交易台走了一个交易员,和我打过不少交道的交易台老板有一天走到我们办公室里,问我要不要下楼去做交易。当然!我想都没想就回答。就这样我开始了我在银行里从事最久的工作:买卖房贷债券。那是2007年初,金融风暴前夕。我刚到交易台上不久,有一天下午,一贯沸沸扬扬的交易台突然变得一片寂静。我抬起头,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突然发现好几个人围在我身后的一个资深交易员的电脑边,我也好奇地走了上去。只看到屏幕上是一页一页的求售债券,好多页。我问老板这是什么,老板说那是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交易台的全部资产,他们在求售。我虽然没有完全意识到事件的重要性,但隐隐感觉到事有不妙。贝尔斯登不久后就宣布破产了。我所在的美林证券也大受打击,先是我们交易台不允许再购买债券,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示我们的交易台已不再正常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客户提供流通性,当客户需要卖出时,我们和其他投资银行一起竞价,购入证券成为我们代售货源,当客人要购买的时候,我们再提供标价,我们在其中为市场提供流通性。很快,有些客户拜托我们大量出售他们的债券,我们自己很多债券也被迫廉价出售,整个市场很快就只有卖家,没有接盘的买家。金融风暴汹涌而来。很快,公司高层人事变动,紧接着我们交易台上开始大幅裁员。每过几星期,就会有口风露出来说,这个星期几是砍人日。到了那天,大家就坐在自己位置上,祈祷自己的电话不要响。因为电话就有可能是人事部打来的,接到就要过去谈话,直接会从那个会议室直接走人。人事部的人会到这人的位置上给他收拾私人物品,帮他拿过去。刚招我的老板很快就被解雇了,我们整个交易台从原来的5个人,变成后来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同时,金融危机急剧恶化。我刚刚经历完的这一轮激烈震荡结束刚一两个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我打开纽约时报,原来以为会读到雷曼兄弟被收购的消息,却无比惊讶地看到头版头条: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我立刻打电话给爸妈,请他们帮我存一点钱,以应急。那是2008年9月。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目睹了一场残酷的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美林证券和美国银行有着完全一样的业务,也就意味着每项业务只有一组人可以存活下来。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那些40几岁的男人,全家十几年全靠他一个人养,突然没了工作,那种绝望的眼神,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对自己发誓: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的命运被别人左右。我幸运地被留了下来,2009年1月转到美国银行的交易台上开始做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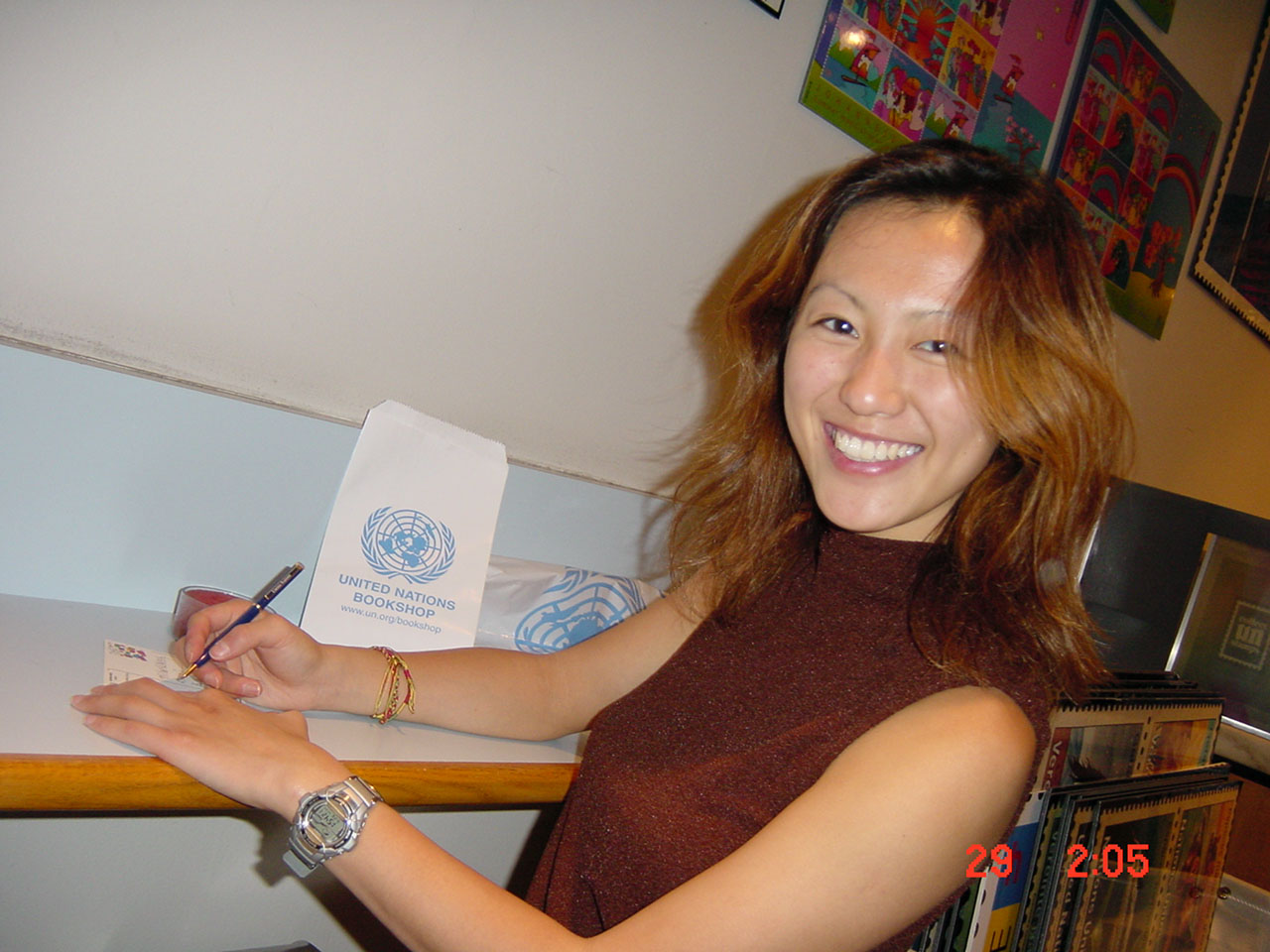
两年多后,我又开始不安现状。我看看我的老板,他们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并不想要赴他们的后尘。每天的工作就是搞好办公室上上下下的政治关系,我知道那不是我。我不想这辈子就这样一直做个只会交易这一种债券的交易员,无论薪水有多高。就在这时,法兴银行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过去帮他们开辟房贷债券交易的业务。虽然还是一样的工作,可是可以从头开始一个新交易台是一个很好的挑战,我兴奋地答应了。那是2011年的5月。
新工作开始之前的“花园期”,也就是旧公司照付工资,我必须不工作,在“花园”里待一下,这是金融界的行规:如果下一个职位是一个竞争对手,必须让他离开一下行业和客户。这段时间对金融人是最为珍惜的,我好好想了下我该去哪里。在非洲的纳米比亚和尼泊尔中,我选择了一个人去尼泊尔。背个大包,用两个星期时间,徒步一直走到珠穆朗玛峰的脚下登峰的大本营。那次旅行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次远行。稀薄的氧气,蔚蓝的天空,无语的雪山。我的脑海里一片宁静,整整12天,每天随着太阳的升落起息,白天爬山,晚上和小客栈里和其他徒步的旅客聊几句,累得8点就睡着了。时间仿佛凝固了,那几天里我不再无休止地寻寻觅觅,我满足地沉浸在那个时刻里。
回纽约后,忙忙碌碌的生活很快又开始了。我尽心尽力地想把新的交易台搞起来。有时候会整晚想工作的事,睡不着觉。2013 年夏天我的大女儿出生了。产假里,我一整天一整天地抱着她,就这样看着她,她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她让我终于明白,如何跳出自己的生活爱别人,什么是全身心地去爱。只要有她在,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是快乐的。我一直记得有一年回家,在城隍庙小商品市场买了一对耳环。回来不经意说了一句,那个耳环的小吊坠我不喜欢。爸爸就拿了工具出来,用心地坐在桌边,开始帮我拿掉那个吊坠。那时已经离家很久了,早已习惯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想要的都得自己去做。当时我看着爸爸眯着眼帮我改耳环,心里非常感动。真的只有自己的爸妈会这样在乎我,无论多么微小的要求,都会上他们的心。女儿让我学会如何去爱别人,如何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前面。
新工作压力蛮大,因为交易台小,没有像美林那种大交易台那样可以用别的交易赚的钱补救出错的交易。除了对我个人的信任以外,客户也没有别的理由来和我做生意,法兴银行没有像美国老牌的投资银行那样提供研究,杠杆之类的辅助服务。我的法国老板对我很好,给我很大的自由,让我做想做的事情。正因为这个,虽然工作艰难,要和像美林,高盛这样老牌的投行抢同样的客户,我还是工作得很快乐。
灾难却无声无息地降临了。突然有一天,我早上刚进办公室上班,人事就打电话叫我去谈个话。一进去,老板的老板告诉我,我和我的老板同时被带薪留职,公司需要对我做过的一些业务做调查,美国证监会对我下了上堂书。我好像被打了一记闷棍,毫无知觉地离开了公司,回到了家。换上牛仔裤,我开始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我从家走进公园,再绕着公园走了好多圈,还记得那天下毛毛雨,长凳上湿漉漉的,坐都没法坐。从早上一直走到晚上,走得再也走不动了,回了家。我把自己扔到沙发上,告诉阿姨我的工作没了。阿姨看着我,告诉我,你不能这样为自己难过。我以为听错了,瞪着她。她指指9个月大的孩子,说:“孩子是可以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的。你必须为了她,让自己真心地快乐。”我恍然地看看孩子,她真的没有像平时那样高兴地迎上来,而且我知道我这个阿姨是不说谎的。第二天早上,女儿醒来,我给女儿吃了早饭,女儿看着我笑着,我放了音乐,抱着她随着音乐跳起了舞,女儿在我肩上笑着,我在她背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起,我对自己发誓,在女儿醒的时候,我不要想这件事。没想到还真的可以做到,每天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可以不去想这件事,还真的不难过。可是晚上她一睡下后,我就无法自拔地感到气愤,难过,哀怨,担心。
原来这所有一切都来源于一个我交易台上的一个助理。助理还不是我自己找的,是我老板安排来我台上的,可是他的个性非常不适合做一个交易员。来了一年左右,我们都觉得他不行。2013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的老板决定要炒他鱿鱼。我对老板说,不能等到明年过完新年吗?他老婆还有几天就要生孩子了。老板说,生意是生意,我们不能考虑太多。几个月后,银行收到助理律师发来的要挟,要么银行给助理赔钱,要么他把我们的一些把柄交给证监会。老板把我找去,给我看了那些被认为是把柄的交易,问我有问题吗?我说没有啊,业内都这样做了好几十年了。我刚上交易台的时候就是先做这类交易的报价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做的是房贷债券,不像股票有交易中心公共报价,一个债券一年出来流通1,2次而已,每次每个债券的报价都需要做半小时到一小时的分析。大的基金有时候把一个债券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债券放到市场上,也就是让几个投行的房贷债券交易台竞价,基金需要用这个价钱来做账。因为这个流通性差的原因,基金会给熟悉的交易员一个暗示,表示他们会再买回这些债券。这样我们交易台的标价不用太仔细,差一点没关系,差太多的话,我们也要吃进。所以作为刚上台的小交易员,很多就先开始用这些单子来练习。我从来没想到,这些“预定”交易是违反证监会规定的。在法兴银行的时候,正好遇到市场很糟糕,我不能买债券。所以当老客户找我的时候,我必须得到法国老板的同意。法国老板因为从来没做过这行,叫我找银行的法务部。法务问我,客户有没有contractual obligation(签合同有法律义务要重新买回去)?我说没有,法务部就OK我了。一直到后来,和公司调查我的律师一起坐下来,我还完全没有头绪,问他们我到底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们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prearranged trading(事先安排好的交易)的定义:只要双方有一个彼此的会意,就算是了,不需要合同。
因为这个错误,美国证监会和交易所分别有各自对我的”惩罚”,我的交易执照被吊销。我才意识到,即使银行的法务部OK了我,也不能减轻我的“罪”,在美国,无知不构成理由。最让我咽不下气的是银行对我的态度。我和我的老板一起被离职调查,一个月后,我被记过开除,老板却又回去上班了。我的律师和证监会在争辩该如何写我的审查报告时,让他们写进去我有通报我的老板和银行的法务部,他们居然告诉我这个是有争议的事实,不能写进去。我才知道,老板和银行说了谎,他们把所有的责任推在我头上。我扪心自问,当只有我和政府的律师在一个小房间里,我是说实话还是说一个保护自己的版本?我选择了说实话。到今天我也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块被丢出去的抹布。银行还告诉我原先的同事们,不要跟我联系,因为怕我转过去告银行。有时候我觉得很冷,大白天钻进被子里,自己抱一抱自己。因为是记过开除,我不能领取存在公司里很大一笔长期分红,也不能领取政府的失业救济金。我担心自己怎么来养家,更气愤不分是非的银行和法律系统!同时,还要面对证监会,因为经济危机就是从房屋贷款这一块开始的,而且老百姓对华尔街愤愤不平,政客们在这个大环境下,特别要抓些房贷债券的从业人员来平一下民愤。我的有些同行甚至被控诉有刑事责任,因为这一行就这几个人,有好几个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有错,可是要遭牢狱之灾绝对是不公平的。每天很怕夜晚到来,因为越到夜深人静,越睡不着。脑袋里一片混乱。
可是到了白天,看到我的小孩,她的笑容温柔地抚平我皱乱的心。她让我觉得,无论我做了什么,她都会坚定地站在我身边,爱我,和我在一起。人们说大人多么爱小孩,其实小孩也是那么爱我们。我亲爱的家人们,谢谢你们在是是非非中,毫无疑问地相信我,站在我这边,拉我站起来。

我决定我不要告银行,我决定不要浪费精力在一场比谁更无耻的比赛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选择的新领域:房地产经纪。在痛苦的那段时间里,我认识到所有自认为永远拥有的东西,转眼间就可能失去。我学会了跳出我自己的世界,为别人着想。在我强大的时候,我没有体会到真正的喜怒哀乐;在我弱小的时候,我却感觉到了真正的快乐:当我一无所有,别人对我的爱护帮助让我如此感激。我希望自己在再次强大的时候,能为别人做到别人为我所做的。
我为什么会选择房地产经纪这一行呢?这还得从我做房贷债卷交易时候说起。我在纽约和弗罗里达买卖了好几次房子,遇到了不少房产经纪。好的中介成为我很好的朋友。我也一直在纳闷,这房产经纪这一行,在纽约这100多年好像没怎么改变。科技让所有行业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为什么房产经纪还是老牛拖车的感觉?所以我很好奇这一行。而且,当年我曾想过要读建筑或室内设计,对房子的设计建筑非常有兴趣。也许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对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都很了解,在这两个地方生活,都觉得是自己的家。而买房子这件事是文化的最终体现,作为站在两个文化中间的桥梁,我觉得自己做这一行很有优势。就这样,两眼一闭就跳下水了!
万事开头难。我每天去办公室,却也没什么事情做,每个月的家庭开销像流水一样的哗哗地出去。那个时候真的压力不小。我的第一个客户是美林招我去交易台的老板。他要租房子,我帮他找了上西区一个联体别墅里的一个复式公寓。到现在还记得我收到那第一笔佣金的激动!我原来金融区里的很多老朋友老客户陆续找我。我也学习了怎么做市场开拓,什么是我的品牌,我给市场带去的价值是什么?这么多经纪人,客户为什么要找我?做了4年,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我觉得我的金融背景培养我对信息和市场的直觉,是我的优势。同时我认识到这个数字时代对传统的市场营销有全新的帮助及挑战,我请到各个方面的专家,帮我把一架功能最齐全,最有效率的战车逐渐造起来。

刚开始的第一年,我的收入居然恰恰是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收入。世界真充满了巧合!我把以前的光荣和耻辱统统埋进了土里,低头一心一意地把新的事业做起来。短短四年,光从收入上来说,就和以前做银行交易员并驾齐驱。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可以左右我的未来!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我对未来充满着期待。

 葛宜珉,女,1979年出生于上海,1997年上海格致中学高中毕业,1997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德语一年。1998年赴美印第安纳州尔汗大学攻读学士学位。2000年赴德国和奥地利游学,攻读德语和艺术史。2002年尔汗大学毕业,获计算机和经济学双学位,德语副学位。本文是作者纪实文学创作的处女作。
葛宜珉,女,1979年出生于上海,1997年上海格致中学高中毕业,1997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德语一年。1998年赴美印第安纳州尔汗大学攻读学士学位。2000年赴德国和奥地利游学,攻读德语和艺术史。2002年尔汗大学毕业,获计算机和经济学双学位,德语副学位。本文是作者纪实文学创作的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