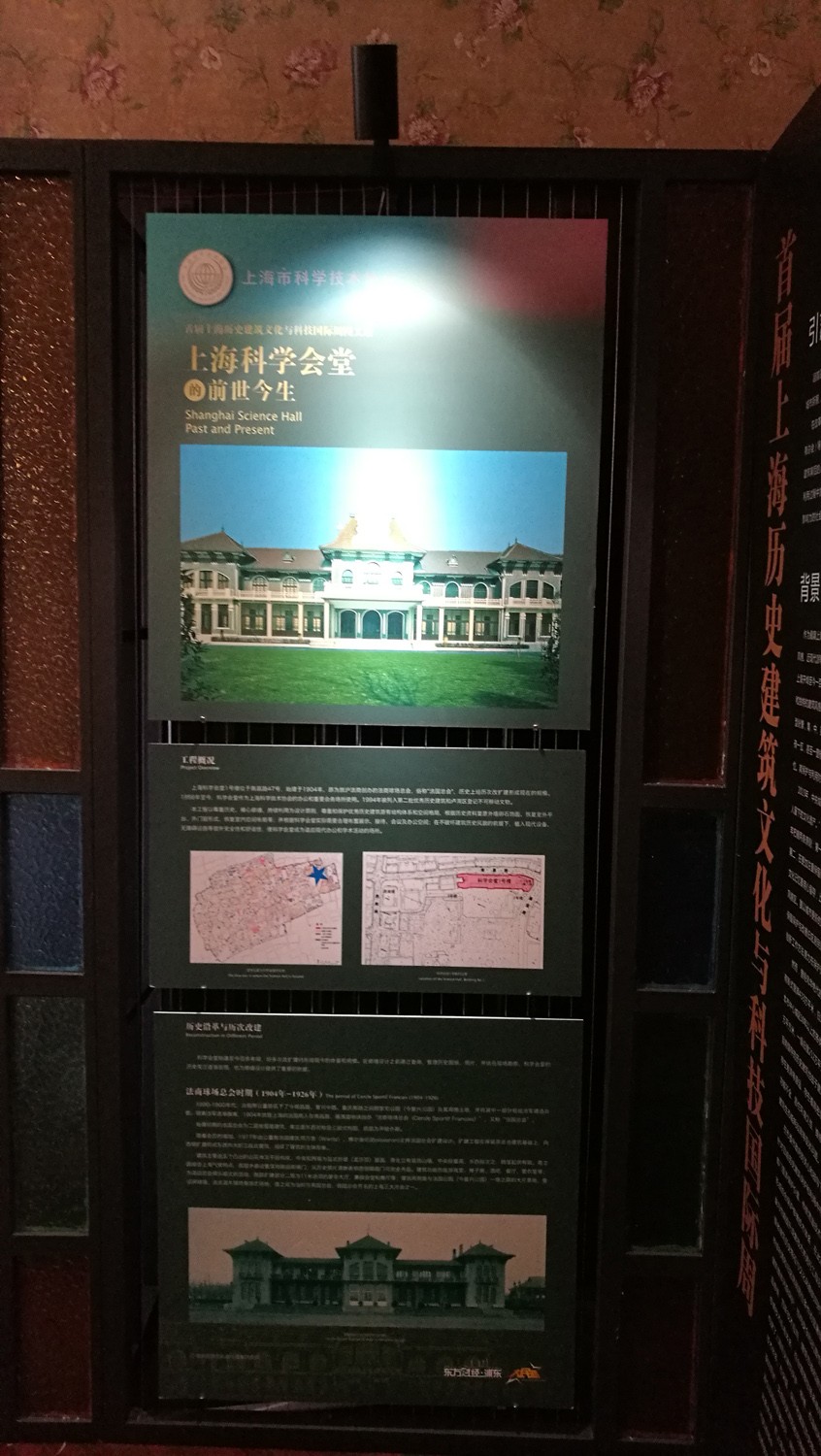有点远,有点近,点滴缘分在记忆
对于一个17岁离开家去复旦大学读书的嘉定人来说,我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是有些不确定性的,上海人?当然。嘉定人?自然。嘉定在上海之内,但原本隶属江苏,后来划归上海,多年作为郊县存在,少时里人乡邻们去市区皆称“到上海去”,是故,自感似乎在上海之内,又在上海之外。诸如南京路淮海路外滩这些名胜自然是如雷贯耳,择机要去走走看看的,但有些则倒可能一直心怀莫名的陌生而尊崇感,尤其那些深宅大院式的机构,名声在外,特地去看看?早些年间似乎可能性不大,就算门房不拦你,自己先挫了几分,比如以“会堂”冠名的,如友谊会堂,文艺会堂,科学会堂,还有作家协会,倘若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就是一个远观的地方吧。
当然,后来,这些“会堂”也还是有机会出入了的,开会等其他。也许,建筑并无分别心,还是人分别了而已。
我知道其实我不必为了写科学会堂绕这么个弯子,顺带把其他会堂也连带了,科学会堂又没有说不让你进去啊,那是你自己莫名小心思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开门不大,却内部宽阔的科学会堂确实不怎么像一个随意出入之处的,再加上“科学”两字,普通民众想想自个人儿和科学沾边不多,那就不进去打扰了吧,尽管内心很期盼进去瞅一瞅。“科学会堂”四个字还是1949年以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写的呢。
曾经在1990年代住过淮海坊十年,淮海坊的一个大门就开在南昌路茂名南路口,我们的门牌号也是按着南昌路来排的,距离南昌路47号科学会堂的门牌,虽然有个三百来号的出入,到底也在一条路上,说不上紧邻,但走走过去也不算太远,沿着南昌路,走过瑞金南路,走过思南路,也就差不多到了。从思南路一直到雁荡路的这一段南昌路,长长的围墙,望过去,中间帽盔式的顶虽不高耸,但在周边的新式里弄房子间还是别样味道,帽盔两边延展出宽阔的两层楼房,拱券窗子一一关着,映衬着路边的法国梧桐,里面是什么呢?大门却是并不彰显的,只有走过细看,才见两扇带彩色玻璃的大门,走进去,法国古典风格的装饰,深色的木质幽幽光泽,彩色玻璃透光又柔光,门廊两边扶梯盘旋而上,正对中是阳光下明绿的花园。倘若刚刚在南昌路瑞金路口的那家饮食店吃完一客生煎馒头,拾掇拾掇衣服,慢慢走进科学会堂,确乎扑面的静气,由不得让你整理心情,拢一拢头发,仿佛要从尘满面的烟火气中退出来,准备好进入另一个时空。其实,它的对面已然是店铺弄堂,它的转角隔壁就是以响油鳝丝水晶虾仁四喜烤麸等闻名的洁而精菜馆。

科学会堂进门处的楼梯和彩色玻璃

科学会堂大楼一景
其实,那些年里也并没有常常去科学会堂。如今倒是有市民没事也去走走看看,底楼喝个咖啡,花园拍个照片,会堂一并容纳的。彼时,倘若去,总归还是有点什么事,感觉中科学会堂是一个开会议事的场所的。说是“会堂”,其实它是一个单位,属于上海市科技协会管理的。有会议厅,有办公室,有报社杂志,有食堂餐厅。这么说来,又似乎使科学会堂不那么神秘了,平常单位里有的,这里都有。当然,平常单位里没有的,这里也还是有的,不日走来走去的人中,也许与你静默着擦肩而过的那个衣着简朴、神色淡然的老先生正是某领域如雷贯耳的科学家呢,他的研究正推动着某个科学领域的空白,到末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休戚相关呢,比如生物制药、器官移植、神经元等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的智性泽光,也是以造福人类为己任的。


南昌路47号的科学会堂
这么一说,如吾等写作者参与到相关的写作中来,并因此而与科学会堂发生了物理空间的联系,也算是并不违和这个空间的气场的。
那些年,常为之写稿的《科学生活》编辑部就在科学会堂内,是一号楼主楼之外的一幢灰色外墙的普通楼房。因为离家近,有时会去编辑部坐坐,和编辑朋友佩英和李乔老师聊聊天,稿子的事,日常的事,聊着聊着,有时会发现聊出新的写作主题。没有手机的年代,面对面的寒温叙谈,比友圈的点赞更能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非科技工作者,自然写的文章还是科学外围吧,科学生活,科学的生活,生活中的科学,有关科学与生活的关系,种种皆是,虽然,以当下之语言之,实在不够“硬核”科普,不过也算在大气层里溜达吧。记得有一次佩英撺掇我参加科协的科学普及部组织的一次征文,名为“‘蟳之宝’杯社区科普读书和征文”。年轻嘛,兴头也足,就写了篇《与信息共舞》参与了,竟然还获得了一等奖。那是2001年前后吧。为了重返现场,查询那些年写着的日记。果然有,如下:
2001年1月10日。下午2点在科学会堂1113室开会。上海“蟳之宝”杯社区科普读书和征文活动暨颁奖,我是得了一等奖的。其实一等奖也没什么,共评了20名,二等奖40名,因为是以社区为基本面的。碰到王佩英,她在会场上忙,忙前忙后的。来的有些是街道的工作人员,说话的,走动的,似乎有些乱哄哄。奖金少得好玩,150元,权且当作稿费吧。
倘若不是日记,究竟多少名一等奖,奖金几何,确实不记得了。那么再翻找,还真找出了那本获奖荣誉证书,签发章“上海科学技术协会”,签发日期“2001年1月”。
记得1113室,是一个蛮大的会场,白色的布椅套,只是会场人不少,确实有些闹哄哄的。不过科普读书广为播布,只要读者众,闹哄哄些也是无妨,可能有不少读者也是第一次来科学会堂参加活动吧,不免小小兴奋的。至于那蟳之宝,不外乎是一种保健品吧,倒也没特别往心里去,冠名之类的活动之前往后如今都是如此的。那次颁奖台上应该还坐了不少科协领导的,可惜非手机时代,也非数码普及时代,大概忘了带单反相机去了,也没留下什么影像。其时,也无所谓晒朋友圈之类的。

科学会堂会议厅之一
有一次去科学会堂开会,应该大概是科普作协举办的座谈会,在一号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沙发围坐,那天在座的有叶淑华女士,一位朴素的亲切的微笑着的科学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于谈些什么,真是依稀仿佛了。19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在文学写作之余也写一点科普主题的文章,关注克隆技术,关注生命科学,尤其关注科学和人的关系,对于一个小学初中时爱读福尔摩斯探案、喜欢科幻小说、每月必读《科学画报》的女生来说,即便后来从事文学教学和文学创作,也是会读一读爱因斯坦、莱布尼茨的文章,也还是会关注一些科学方面的书籍,比如梅特里的《人是机器》,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和《水母与蜗牛》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文学和科学,心灵的宇宙,身体和大自然的宇宙,都不可偏废,都帮助一个人生命视野的养成和拓展。曾经在2001年于《世界科学》杂志上连载了多期的关于科学人文的文章,也算是在科学人文领域内的一点尝试。也曾经是上海科普作协的会员,有一年换届,还去科学会堂与会了的。虽然进入21世纪,也还是会写一点由科技话题生发的随笔(身于目下,科技发展加速度,延展到日常生活中,比如各种智能应用,没有人能置身度外的),但创作的主题还是多在于文学艺术方面,科普作协的活动就渐渐很少参加乃至几乎退出了。虽说如此,科普文章也还是会经常看的,微信发达,各种真伪信息,也实在需要科学理性的头脑来辨识思考的。这么说来,真是很希望科学会堂跟普通民众的距离近一点,更近一点,科学家们能将真正的科学知识科学理念推布给大家。
那天,己亥年暮春,从一号楼主楼走到思南楼的途中,在思南楼大厅里看到一面循环播放的院士电子墙,很有创意的展示。看着一张张或亲切或沉思的面孔,想着如果让更多民众来了解院士们做的研究,院士们也通过一定的渠道(比如科学会堂微信公号诸如此类)跟普通民众说说手头的工作,说说前沿的科技进展,说说跟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那些发明发现,也许某某保健品名不符实甚至害人不浅的陷阱也会少些吧。
在它安静的周围
科学会堂通常是安静的,即便有会议活动,有历史有故事的老房子大草坪,似乎都能将之熨平。不过,一样有历史有故事,它边上的洁而精川菜馆却是人声鼎沸的,1927年创立的老字号了,菜式口味纯正,常常一座难求,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其味无穷”醒目于墙,不过据说真迹已藏,高仿在挂。说是附近曾有对老夫妇几十年如一日来此吃饭,座次固定,菜式固定,持久情怀。几年前经媒体报道一时传为沪上佳话。饭店对面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枣红砖墙则看着温雅,这是1917年5月由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士创办的群众团体,其“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理念有力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也是与海内外侨胞及教育团体的交流桥梁。历史实在悠久,值得网搜深度脑补。
这么说着,就好比说是看看科学会堂,顺带着还感受感受其周边的气息,这些气息各不相同,却抟成一种特有的场域,徜徉期间,是不知不觉染上一些别样了的。
比如假如你是从南昌路自西往东的,那么离科学会堂咫尺之间,南昌路53号是值得先驻足看一看的。看什么呢,不过一株法国梧桐后的二层小楼,却是融合了中西绘画精华而自创风格的大画家林风眠在上海的故居。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离沪定居香港,在此住了25年,期间,林风眠有去农村渔场采风,也有1968年到1972年因外籍妻子而被以“特务”之莫须有罪名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但是,无论如何,无论身心如何遭际,也哪怕法籍妻子携女离开中国只留下他孑然一身,只要在这间小楼,二楼画室的灯总是亮到很晚。

科学会堂周边·南昌路53号林风眠故居
孤寂的岁月里林风眠的艺术之火熊熊燃烧着,在画家心里,在那些仕女、静物、风景中。哪怕几乎为喧嚣的世俗所忘却,哪怕肉身的生活寂寞拮据,林风眠的精神一直激情于线条、颜色、勾画这样一种人类情绪的原始冲动中,这种冲动乃艺术之本质。林风眠说:“艺术是感情的产物,有艺术而后感情得以安慰。”林风眠的绘画总是让人感觉情绪的流动,如私语如感叹如心的悸动,他的大部分作品似乎总弥漫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飘渺的相思,一份沉沉的寂然。孤寂的生活提炼出林风眠艺术的纯粹,也提炼出一种优雅寂然的美学。仿佛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美丽似乎触手可及,但却是飘渺悠远,“庄生晓梦迷蝴蝶”。可是,老画家在这里画出的许多得意之作,却无奈在那风雨飘摇的“文革”初始将数十年的画作,撕碎,浸入浴缸捣成纸浆,冲入厕所。而不少作品正是当年抗战胜利后画家自重庆返沪,上飞机扔掉行李携回的。看一眼那棵法国梧桐,想象在画室里画家如醉的创作,画家一勺一勺将画作纸浆冲入抽水马桶的画面同时浮现。这些都是画家壮年所作啊。曾经在南昌路这间屋子看过林风眠画的作家木心(他是林风眠的学生)写道:它们“像/花一般的香/夜一般的深/死一般的静/酒一般的醉人 这些画,保存在时光的博物馆中,越逝越远。”窗外的梧桐应该看到了,默然,伤痛,落叶飘零。时光确是越走越远了,却没有远逝,越来越让人不能释怀。
每每走过林风眠故居,常常想起他的那幅《孤鹜》,飞翔于沉沉的天空,虽然乌云密布,风雨欲来,可是它们勇敢地飞着。黑黑的画面不同于林风眠仕女画的优雅甜美,感觉到画家内心的另一面,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敏锐,那一种风雨中的勇气和力量。类似水墨浓重的画在1974年被当时的“四人帮”一伙批判为“黑画”,使林风眠精神上遭到极大折磨。但,为艺术而生的生命、信念支撑着林风眠的一生。定居香港后,创作不息,直至91岁高龄还在画画。如他画笔下的白鹜,淡淡水墨,轻灵地展翅于芦塘间,提足振翅漫步觅食,总是优雅,艰辛好像都隐没于湖水深处了。
钱君匋先生回忆林风眠时,说过一件往事:1968年到1972年“文革”期间,因妻子法籍之故,林风眠被以“特务”罪名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反铐双手,吃饭时也不给松开,古稀之年的画家只好埋头进随身带入牢监的一只小面盆舔食。往事与画家创作的轻灵的白鹜画面不断闪回,无法言语。
近年南昌路53号边上曾开出一家情趣用品商店,说是51号,但紧挨着,令特地去画家旧居拜谒者顿感失落,莫名所以。一时也引起一些舆情。不过,己亥初夏时特地再去踏访,53号边上的铺子做了房产中介。窃以为,林风眠先生若在世,依然住在这里,二楼画室内的笔墨不会因此介怀这些,孤鹜照旧飞翔,仕女终是恬雅。
当然,科学会堂周边不止有林风眠故居这样的人文地标,附近的新式里弄房子里曾经走来走去不少时光里的各式人物。比如69弄3号,演员赵丹1936年曾住过,弄堂深处的那块门牌很剥落了。再比如136弄里的11号二楼,诗人徐志摩1931年曾寓居于此,应该是和陆小曼琴瑟相谐之时,后来他们迁居去了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四明村。再过去一点,离开科学会堂略有些远了,南昌路180号,现在挂了家公司牌号,却是有渊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旧址”的铭牌在门口围墙上烙印着。科学会堂周边的南昌路,民居商铺,日常生活里从来都折叠着历史人文的皱褶。记得附近有间红木家具修理铺,私人开设的,穿着泛了白的蓝卡其中山装,那个老头总在忙碌,红木家具在民间的温度其实从来没有冷过,1990年代间每次走过,从来看不清老头的脸,他不是俯身打磨,就是低首油漆。好的手艺活正是满满的技术活啊。到了2019年春天里路过,却已经改换门庭为古董商铺了,直觉中与过去的旧红木家具铺子一定彼此渊源。
如果,走累了,思南路拐弯,过复兴中路有思南公馆可休憩可咖啡,也可看看法式风情的老上海建筑,还有周公馆、梅兰芳在沪的旧居等可踏访。若随意些,不过复兴中路,思南路那家坊间口口相传的阿娘面馆也不错。当然,阿娘如今是不在了,面馆由其小辈打理。上世纪九十年代去思南路上的那家邮局办事,去过好几次阿娘面馆,彼时的阿娘面馆离邮局很近,就是阿娘自家门面,阿娘那时七十多了吧,下面不必亲自了,浇头也不必亲炒,但原料、配方一律阿娘调理;就是面,也是阿娘亲自挑选工场,监督质量,一间大概就十多平方的门面,还连着厨房,坐不到桌子的有的就站着吃,后来阿娘扩大再生产,对面盘下间铺子,宽敞多了,一碗面就这头端到那一头,中午时分尤为景观,阿娘面是周围商厦众多职员的选择。阿娘秘制的咸菜肉丝可以添加,不大的碗,她从碗橱里取出,拨出一筷子,得的人此时十分满足。阿娘面在上海美食指南之类的媒体节目上都风光过。
或者,也可以去淮海路走走看看。又或者,从科学会堂出来,到雁荡路,找间餐厅吃了饭,去复兴公园坐一坐,看看锻炼的下棋的老人,看看手推车里的小孩子,看看高大的法国梧桐,也是浮生闲趣。
围绕着科学会堂,这一带的风貌是且精致且日常的。宽窄适度的马路、街面、社区、商铺和公共机构,讲究的老建筑有之,普通的民居有之,修缮装饰风格化的铺面有之,路和路之间有弧形的拐角,不是直角的尖锐,那些路边的事物也都是有年头了的,可以慢慢地走一走,不必太赶时间,拉长心理和情感的时间,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和爱人相对的炉火旁,再久的时间也似乎是刹那。
苍翠袭人衣,科技渗日常
和外子说起科学会堂时,难得回忆过往的他倒说起的一段旧事。那时上海科协主办的《上海科技报》在报社门外,也就是科学会堂南昌路的围墙那里,曾经是设有读报栏的。1980年高考前,他几乎每天去报栏,看彼时的《上海科技报》刊登的数理化习题专栏。那个年代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少,除了学校教学,课外补习寥落晨星,更何况高考复习,如今各种补习班真题试卷已然产业化了。他说每天去看看读读想想,颇有启发。也许当年他考上华师大物理系,《上海科技报》的这个专栏助力不少呢。如今的科学会堂外墙安排有声光电多种元素而成的展览,文字的阅读让位给了多媒体的多方位展示。报栏消失了,往事并不如烟。

科学会堂5-科学会堂内部空间一隅
我们说着说着,自然就想起了一个人,一位前辈,华师大的王一川老师,他化学专业出身,热爱科普写作,当年外子就选修过他为理科生开设的科技写作课。王老师投身于科技写作经年,编书写稿,忙碌充实。外子毕业后,与王老师一直保持联络,参与王老师主编的科普书籍写作。王老师言语爽直,月旦人物时事。倘若他去科学会堂开会,一般都会来南昌路的我们家。那时没有电话,他就直接楼下呼唤,有人在,就上来坐坐,无人则打道回府。几次倒是我在,听到喊声,先请他上来,泡茶备点心,有什么吃什么,乔家栅的团子、哈尔滨的西点,再设法通知外子,接下来必是一通王老师的天南地北。茶喝了,点心也吃了,闲话也说了,王老师拍拍衣裳,起身告辞,回他在华师大的那间陋室去了。这好像成为他到科学会堂开各种会议后的余绪。
王老师的家,如同一间宿舍大小,和太太一起,两张小床几乎并排,房间已去大半。居陋室,教学写作,主编《世界大发明》丛书(我和外子都参与了其中两本书的编著写作),王老师还主持编写《化学之谜》等等,直至六十岁出头病逝。
2019年初夏,讲到科学会堂就想起了王老师,1990年代的事情瞬间回到眼前。时间,总在流逝。时间,也似乎可以停止。停止在它愿意停止的地方。
虽然王老师走得早,但我愿意相信他是到了星辰灿烂的浩瀚中去了。那里有更多的迷激发他探索的激情和想象吧。好比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歇过,火箭,卫星,载人太空器,乃至火星探索的计划等等,科学工作者们一直在扩展着人类对头上的星空了解之边界,就是文艺领域内,从早先《未来世界》、《星球大战》到如今琳琅满目的科幻电影,诸如《阿凡达》《星际穿越》《火星救援》《降临》《星空探索》《流浪地球》等等,让人都来不及看过来。国外的暂且不说,国内的诸如《三体》引领之下的科幻小说当下也是颇为兴旺。虽然人类世界的很多现实问题每天都在次第出现,并尚待解决,人性的各种善恶美丑等各种幽邃尚待人类本身去认知了解,但人类对未知未来的期待似乎从来没有降低过热情。不过,也许对外太空的渴望了解和探索,无论太空奥秘还是外星生命,其实也出于某种人性,也许也因此而回到更多的人性自我认知。所谓,明面科幻,内部还是人的问题吧。
好比《星际穿越》一片中,上校级宇航员罗伊(ROY)专业素质极强,热情于外太空探索事业,却冷漠于家人和家庭生活,甚至是自闭而孤僻的。但在阴差阳错接受任务去寻找在太空失踪二十多年的父亲的旅程中,在终于于海王星找到已然坚持在寻找外星生命的父亲时,在听到父亲亲口承认这些年来从未关心和爱护过自己的家庭,包括罗伊这个儿子——在同为宇航员的父亲眼中,罗伊更是一名伙伴,在罗伊想带父亲回地球——回家,而父亲还是切断安全绳,消失于茫茫宇宙……这一次穿越光年的任务,罗伊找到了父亲,也找到了“潮涌”的真相,虽然无力挽回父亲,他只能摧毁了父亲的飞船,只身返回地球,但同时罗伊因此而完成了自身生命和心灵的救赎。“你情愿寻找陌生的新事物,也不会关心身边所爱的人”,这句话是罗伊对父亲说的,其实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检醒。回到地球,罗伊仍然对着计算机汇报自己的情况,但罗伊微笑着,神态放松,罗伊懂得了感受当下生命中的所有,他和妻子再续情缘。他明白了,人类所有的渴求和期待不在外太空生命那里,而在人类本身,在人类内心的信靠中。也许这是人类的孤独宿命,但何尝又不是人类之为人类的使命呢。
所以,其实我还是更愿意王老师在另一个世界里探索着科技奥秘,但更开心健康地生活着的。
最近翻出两本书,200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清澈的理性》和《蔚蓝的思维》,皆有名为“科学人文读本”之副标题,里面分别收录了三篇拙文《和尚·DNA·“我”》、《生命是一种偶然》和《敬畏生命》,回想起来当初接到被收录的通知,略感意外之余也是欣然的,其实不算是“硬核”科普文,倒也不无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一种思维连接之尝试。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兴趣其实并没有减少,反而因了科技对生活的各种深度改变和影响而由不得人不去关注的。这么说来,作家福楼拜的那句话如他笔下的“包法利夫人”那样已然也是深入人心的,福楼拜说“越往前走,艺术越是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人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会和”。想起19世纪后半期兴盛的印象派画派,画家们户外写生,注重光影和色彩之间的微妙变幻,除了画家们对以往古典传统画派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外,其实也和当时颜料工业的发展分不开的,便于携带的管状颜料的发明使户外写生成为可能。光影间的妙不可言里也该烙上化学工业发展的功劳呢。
想起科学会堂内一幢楼的外墙上设置的“科学艺术长廊”,一物对应一位科学家,物之造型与相应科学家的发明发现有所关联,如霍金、爱迪生、居里夫人、孟德尔、法拉第……等等,这些名字和事物,都不仅写在了人类文明史上,也镶嵌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电灯电话,激光CT、手机遥控……

科学会堂院士墙
2019年四月的某一天,在科学会堂一号楼咖啡厅,见到时下任科普作协秘书长的江世亮先生。当年我的那些科学人文随笔正是因江先生的约稿而连载于《世界科学》的。他后来去了《文汇报》工作。如今在上海科普作协任职。一别经年,如今再见,自然说起不少当年往事。他热情地说:你以前就是科普作协会员,现在只需要重新登记下,即可恢复,你来吧。我说现在虽然也还写一点和科技相关的文章(智能科技发展的当下,其实每个人都与之有关的),指导过的好几个研究生倒写过科幻小说,不过自己写的似乎属于“软科普”一类了,数量也不算多,主要写作主题还在文学艺术都市人文方面,似乎是不够格啦。江先生连连说道:你客气了客气了。你考虑一下吧。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想,以我欢喜顺应心性的脾性,就不必一定要什么会员资格之类的了,关注或者写作科技主题,不过是生命的一种生发。自然的发生,最是好的。好比,像科学会堂这样的地方,想到了,进去看看,自然会有收获,倒也不必“诸如打卡胜地”之类的,反而不会走心。而科学技术,已嵌入日常,电子支付,网上购物,哪一样不是呢?当然,科技从来也都是双刃剑,不说黑客入侵电脑系统这些,人工智能、克隆技术、核能等,哪一项的发展都考验着人类智慧和伦理,人究竟在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将自己带向何方,这不是技术能回答的,还有赖于人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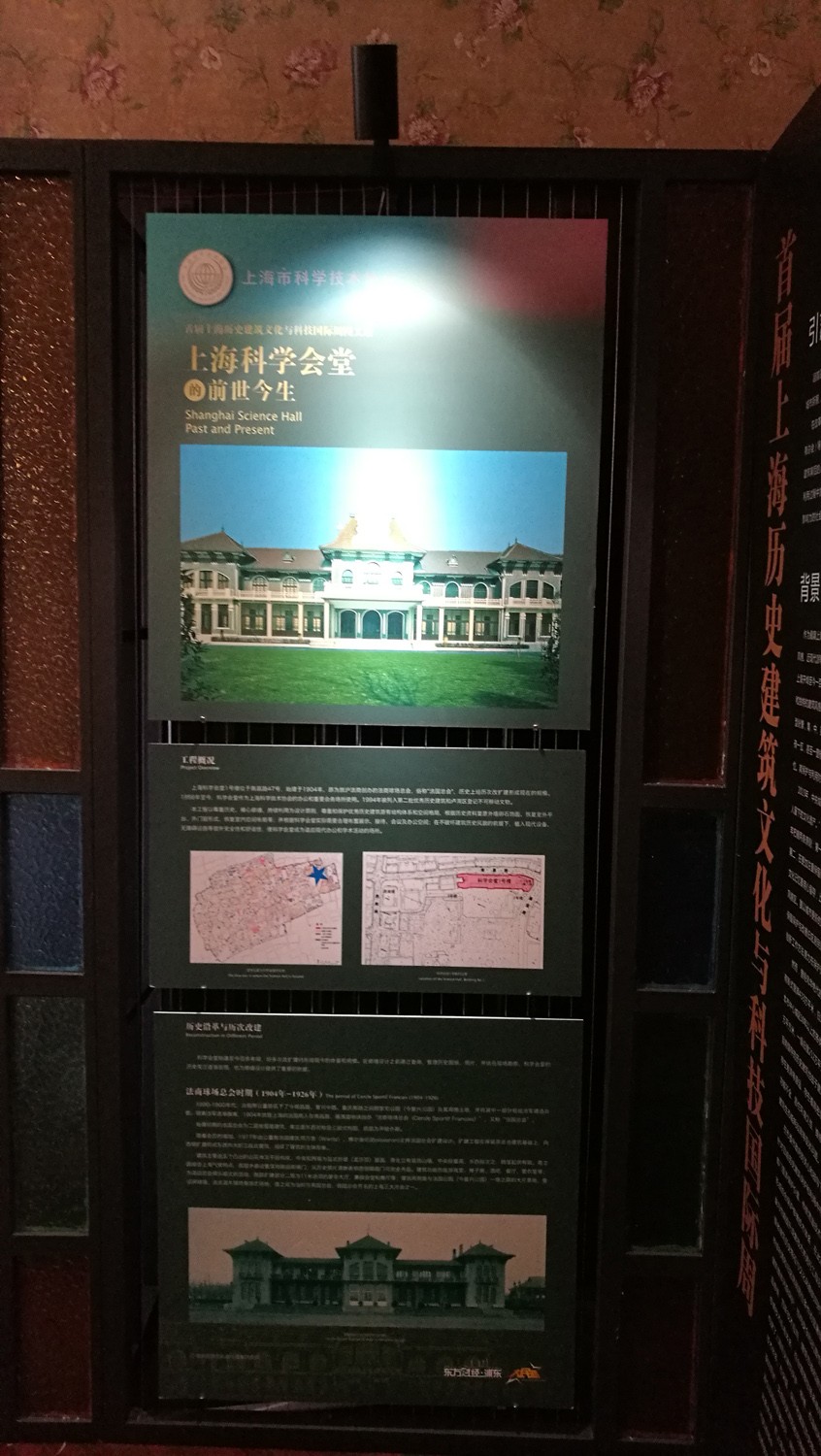
科学会堂内“首届上海历史建筑文化与科技国际周”之“科学会堂”图片
莫名想起王维的《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袭人衣。”当今的人类确乎不知不觉走在了科技的一片苍翠中,也确乎带来很多的明丽,只是浓郁的翠色里,深山苍茫,寻山之路漫漫兮。
(摄影:龚静)

 龚静,上海嘉定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出版有《西门,西门》、《花半》、《遇见》、《行色——龚静散文精选集》、《书·生》、《写意——龚静读画》(初版和修订版两种)、《上海细节》、《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要什么样的味道》、《文字的眼睛》及《城市野望》等十多部散文随笔集。
获第三届“上海文化新人”荣誉称号(2000年)。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2006年)
。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2014年)。2014和2016上海市作协会员年度作品奖励(散文集)以及其他文学奖项。
作品被收入《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散文卷》、《繁华与落寞》、《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你可以信赖他——‘2002笔会文粹》、《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2004笔会文粹》、《新时期嘉定作家群》(作品卷/资料卷)、《清澈的理性——科学人文读本》、《2018民生散文选》等多种散文选集。作品曾经被翻译成英文收入选本出版。诗歌入选《上海文学》英文版首刊。作品曾收入上海市高中语文课本。
龚静,上海嘉定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出版有《西门,西门》、《花半》、《遇见》、《行色——龚静散文精选集》、《书·生》、《写意——龚静读画》(初版和修订版两种)、《上海细节》、《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要什么样的味道》、《文字的眼睛》及《城市野望》等十多部散文随笔集。
获第三届“上海文化新人”荣誉称号(2000年)。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2006年)
。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2014年)。2014和2016上海市作协会员年度作品奖励(散文集)以及其他文学奖项。
作品被收入《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散文卷》、《繁华与落寞》、《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你可以信赖他——‘2002笔会文粹》、《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2004笔会文粹》、《新时期嘉定作家群》(作品卷/资料卷)、《清澈的理性——科学人文读本》、《2018民生散文选》等多种散文选集。作品曾经被翻译成英文收入选本出版。诗歌入选《上海文学》英文版首刊。作品曾收入上海市高中语文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