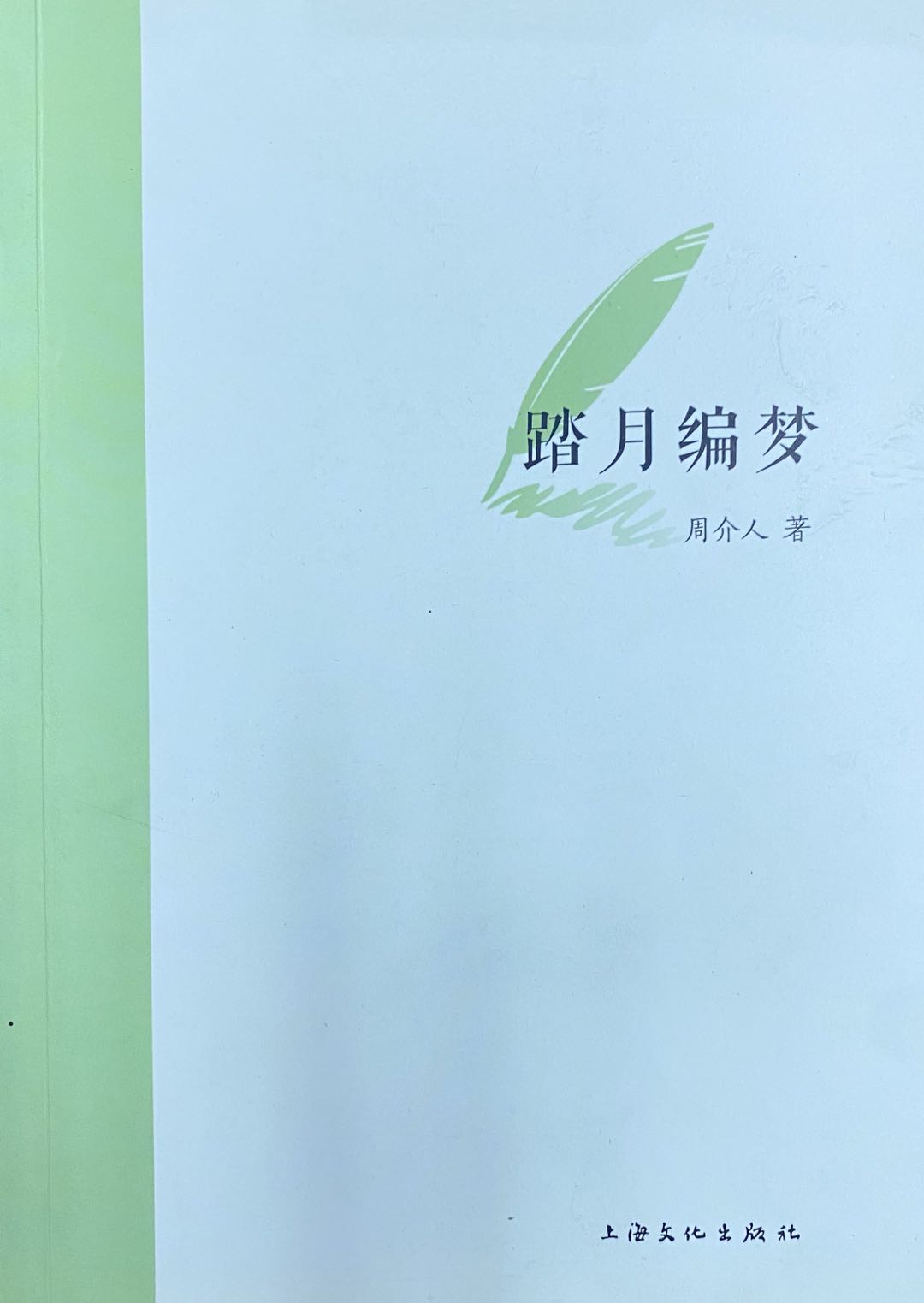五年时光,何况还是跨越世界更替的五年,真的可以说是恍若隔世。当年的印象逐渐变得模糊,一如周老师那瘦弱而坚定的身影渐行渐远,不再清晰可辨,人们记忆中曾经的悲痛和感喟似乎也早已日喻淡然。这是一个容易遗忘的年代,唯一能够激活我们心灵神游的是静默积淀于《上海文学》厚重册页中的诸多经典篇什及其智慧的印痕,其间自然也包含了周老师所经久奉献的一腔心血与挚爱。
平常日子里,我们肯定还会时常念及他的名字,那是因为他和太多的文学事件、历史场景紧密相关,无法剥离。我们的脑海中会时常闪过他步履日渐沉重的背影,还有更多他的亲和力和睿智的目光,那是因为他的身上牵系着文学太多的荣辱悲欢,以及说不清理还乱的世道沉浮和人心变幻,而他始终以一己的宽宏情怀予以化解,唯有文学、文学杂志的艰难时运及自我困境才真正令他忧心不安,殚精竭虑,直至生命飘逝的最后一刻。
他真就像曾经绚烂绽放、凌空飞舞又终将萎的花朵,“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宋祁《落花》)。如今,章台人去,因骨遗香,面对当下纷杂的文学情境,我们在内心深处倍加怀念周老师,怀念他在艰难困苦中尽情凸现的不屈不挠守护文学理想的品格风范。
往事已成云烟。但当安静下来的时候,走在《上海文学》所在作协大楼面貌久远的廊道里,却常常会觉得时间似乎是凝固而苍老的,仿佛迎面就能触碰到穿越而过的真实历史。

上海作协
我是在文学即将从辉煌峰巅滑落的1986年正式进入《上海文学》工作的,更是在周老师等许多前辈师长的关心和呵护下,才慢慢体味出作为现今年代一名文学杂志编辑的甘苦与酸楚。那时候,我们曾经在愉悦与惊异中竞相传阅了已经进入复审、引人瞩目的《访问梦境》的原稿,印象深刻的诗,李陀老师当时来访编辑部时就已经较早肯定了这部作品,他更是旋风般地带来很多新鲜的话语和文坛的讯息,感染着大家的情绪,其高声谈笑状,至今仍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在编辑部所经历的思想氛围最为活跃而热烈的时期,细细回味就如同对八十年代文学兴盛时期那种梦境般景象的又一次造访。当时的周老师正直盛年,精神焕发,常见他一旦读到好小说就喜形于色,匆匆在发稿单上写上几句,然后快步穿过走廊到另一房间与责任编辑交换意见。他性情温和但作风干练,且富有敏锐的艺术眼光,其时他个性化的领导魅力已经深获众心。
在激流涌动的改革大潮中,文学时时见证着一个时代的种种纷繁变化。周老师主政杂志社工作后不久,作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性质的《上海文学》即由于各种原因,不再享有财政及主管部门的任何补贴。虽然束缚少了,但实际上的自负盈亏,本身暗含着很大的市场风险。与此同时,文学、文学杂志首先遭遇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调节下的文化环境和阅读时尚的冲击,开始逐步出现颓势。一时间人心浮动,心理失衡,现实环境的限囿和利益诱惑的驱动,使许多人纷纷寻求起体制外的发展机会。文学杂志在面临更大经济压力难免日显窘困的时候,早已无奈地将一道道深深的时代勒痕印在了自己原本羸弱的肩上,而此时带领《上海文学》负重前行的,正是一介书生、并不善舞长袖的周老师。
起初,杂志社的经营状况还是不错的。在当时“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和“以文养文”的观念背景下,《上海文学》是国内较早创办作家与企业家联谊会的文学杂志,还较早开展了如今各竞相效仿的长篇增刊、通俗文学丛书和写作参考丛书的出版业务,形成了多元的经营手段和发行渠道。在周老师的全新操持下,《上海文学》下设编辑部、书刊经营部、“作家与企业家”编辑部(具体运作作家与企业家联谊会)三批人马,同心协力,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这一阶段相对而言称得上是《上海文学》的经济兴盛期。私下里周老师甚至设想,将来有条件的话,《上海文学》要建立一个思想研究室,专门为刊物的开拓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判断。

“新市民文丛”封面
着眼于文学杂志自谋生存之道的长期行为,周老师那几年曾在大小会议上,适时地提出了“小编辑,大管理”的六字方针,明确强化了经营管理、经济运作对文学杂志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虽然当时它对自恃清高的编辑人员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在编辑部内部引起过持续而强烈的心理震动,但从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深谋远虑。加入一家杂志社不能建立一套完善有序的管理模式乃至经济运作方式,刊物本身不能真正融入市场观念,形成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它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生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失去了企业家的慷慨赞助以后,尤其是从1996年开始的与《劳动报》合作联办的八年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主动拓展自身的生存发展,结果逐渐丧失刊物的生机,处于尴尬窘迫的境地。这是我们至今难以告慰周老师的切肤之痛。
对《上海文学》来说,历史的记忆首先是由经典之作的耀眼名字以及感动人心的独特细节凝聚而成的,那十余年也不例外。它们的字里行间,虽然看似没有周老师留下的个体痕迹,事实上,却蕴涵了他全部的创造性智慧与心血。
1987年以后,作为评论家的周老师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了小说稿的编发中。他将自己的文学判断和理论创造完全融入进《上海文学》这本杂志品格建构的过程。他每期精心撰写的“编者的话”浸润着自己的文学理解,敏锐深广,独具慧识,至今无人可比,成为杂志的一大看点。许多作家拿到《上海文学》务必先看的就是“编者的话”,山东作家刘玉堂就认为“它对文学思潮的归纳,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极具权威性。还有它亲切的语气,用散文化的语言表述理论问题等,都十分具有亲和力”。
其实,最初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原名并非叫《一个产业工人的一天》,而用的是另一个比较匠气的名字,是周老师亲自为之改题,并写文章大力推介,才直接促成了此后“新写实小说”在文坛的兴起。1996年初刘醒龙《分享艰难》的命名则更为文学圈内人知晓,它甚至一度引起了争议,但直到现在仍是一个使用率颇高、指涉复杂的赐予。当时,常常有一些毫不起眼的作品,作者更是名不见经传,然而周老师却能慧眼识珠,稍加修饰,便点石成金,使之顿然生辉。虽然其中大部分作品并未能流芳至今,但周老师的文学识见自成一家,卓具影响,这也使不少当初受其提携的作家如今依然对他心存感激,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情。
在1993年1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周老师甚至将一位苏州青年作家的小说定名为《走出困局》,尽管似乎失之直白和概念化,却无疑满含着他的一种热切的期待,既直接指向新的社会格局下复杂矛盾的化解,更是以隐曲的方式由衷地希望文学同样能够从容解决好市场化条件下的生存难题。在当时文学杂志经营状况大都日显艰难的背景下,周老师独撑危局的苦心和诉求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文学》1993年封面
显然,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仍然得以延续自己的影响力,关键在于我们拥有了周老师这样的灵魂人物。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敏锐的现实感受力和推陈出新的勇气,引导杂志牢牢把握时代心灵的脉动,细致探寻文学潮流的变化。而从他偏爱和力推的作家作品的整体倾向来看,也无疑更注重开掘文学在如何把握转型期中的社会利益格局与人际关系方面出现的新鲜因素。他从来就是与时俱进的,更是一个清醒务实、具有创新思维的文学领军者。
早在九十年代初,面对沸腾的经济大潮,周老师就在“编者的话”中明确指出:“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无法代替精神的绿地。我们坚信,人们最终希望文学所能给予他们的,是人生旅程上的光和热。”1994年2月,他在推出刘继明等一些作家作品的同时,更是直接提出了“文化关怀小说”的概念,将它们放在现代化加速进程历史阶段中所必需的文化反思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年中,他又通过媒体和各种方式,首创性地提出了“关怀现实生存,营造精神家园”的文学课题,为自己杂志的品格追求,确立了独有的标志性话语。“对弱者,关怀他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的灵魂。”这在当时是一句颇为引人瞩目的文学告白。他试图要“使历史进程中的强者与弱者都在文学家园中感受到被理解、被抚慰、被宣泄、被呼喊的关爱”。虽然,“精神家园”的提法,如今谁都可以借此商业化地神圣一把,以期自我加冕,但在当初,它却是一种振聋发聩之声,大大冲击了沉寂已久的文坛氛围,重新唤起了知识分子岗位价值的尊严和自信,更在无形中吸引和凝聚了在市场竞争的严峻生态下渐显失落无助的寂寞人心。之所以说这是《上海文学》一种难以模仿、不可复制的精神标识,乃是因为它不但是周老师率先启悟并郑重提出的一种文学理念,更由于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它早已将众多经典篇什和精辟言说融入了杂志本身的历史血脉,形成了一种特色性的品质和风范。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离不开周老师充满诗情的理论概括力和文学想象力。
1994年末,借第六届《上海文学》奖颁奖活动在本市中山宾馆举办之机,周老师亲自主持了以“面向新世纪的文学”为题的学术讨论。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讨论会的情景,不大的宾馆会议室里聚满了来自各地的作家、评论家、王蒙老师有关文化专制主义的宏论,作家李锐极富个人特色的慷慨陈词,许多的场景仿佛仍在眼前闪现。然后,次年1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王蒙老师的《沪上思絮录》,而李锐则在随后寄来了随笔《虚无之海,精神之塔》。事实上,当时周老师最为关注的,就是面对一个世俗型经济社会的崛起,作家们如何主动调整自己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思维习惯,以应对新生活的挑战。他既希望到了九十年代,知青一代作家能以凝重的理性智思舞动感性的艺术精灵,继续创造“未了”的辉煌,更愿意亲手为知青一代作家之后又一批实力作家在文坛的全面亮相筑就表现的舞台,开启成功的帷幕。可以说,九十年代中后期刘醒龙、池莉、邓一光、张欣等一批作家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在文坛厚积薄发,引人关注,正是有赖于这一阶段像周老师这样具有精心谋虑的杂志主持人所全力推动的思想孕育,乃至依靠理论造势所进行的实际运作。不论对他们的文学价值存在多少争议,但如果缺少了这样的前瞻性思考和开拓性实践,一家文学杂志显然很难凸现自己的个性面目,更遑论建立一种特色性的影响与追求。

上世纪90年代,周介人(中)与茹志鹃(右)、张炜(左)在一起。
1994年12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周老师在扉页上留下了刻画知青一代作家如何思量九十年代的“经济遮蔽”现实,力图实现自我提升的某种“了犹未了”之情的精彩感言。其实,作为文学评论家和杂志领军者的他,其内心的思考与激情、矛盾与探索又何尝不是涌动在“了犹未了”之间?那是,杂志的经济压力日愈沉重,依靠企业的赞助也越来越勉为其难,周老师肯定已身心疲惫,难堪重负,而唯一能支撑他的,正是对此生自己所挚爱的文学的一番未了之情和不悔之心。
1994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文学》连续推出了两个打破传统文体分类的栏目“世事浮沉”和“都市歌谣”。次年,周老师又亲自组织与《佛山文艺》联手筹划举办了“新市民小说联展”及其评奖活动,一时引起众说纷纭。那时候,他不但积极提出了新市民小说的文学主张,力推一批反映城市世俗生活的小说以及文学新人,甚至还经常在卷首语及其他文章中引用一两句诸如《涛声依旧》之类的流行歌曲的歌词,煞是有趣,亦含诗意。我们都对他说,周老师你心态比我们还年轻啊。现在想来,这一切会否是日显疲累的周老师在精神心灵上的一次回光返照?
实际上,他倡导“新市民小说”,绝不是单纯为独树一帜,炒作一番,其初衷明显是在于积极回应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的社会变化,让文学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并且与《上海文学》同时开展的关于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理论探讨相衔接,寻找出一种新的创作路向。尽管由于生活积累、思想储备和叙事方式的局限与不足,这一类写作过多观念演绎,终究流于浮浅,未能产生预期的影响。但是,由周老师领军的《上海文学》在八九十年代能够数度开启风气之先,引导文学潮流,激励艺术创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赢得了历史的荣耀。
去世前的两年,周老师一直苦苦思考着的问题是:当代文学如何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思想分歧与叙事危机?如何解决在时常经济条件下文学与读者、与民间的交互关系?如何从审美上把握改革开放以后的“乡土中国”,尤其是“城市化的中国”?如何开始站在现代都市文明的立场,来看待现实生活及其文化嬗变?当然,这些对他来说本来就不可能是完成时态的精神提问,急剧变化的现实情境本身也在悄悄改变着他的思量和期待,改变着他的激情和梦想。如今,他的生命已然停息,但由他提出的一系列文学思考却值得继续,并且足以延展到当下的中国现实,因而极富前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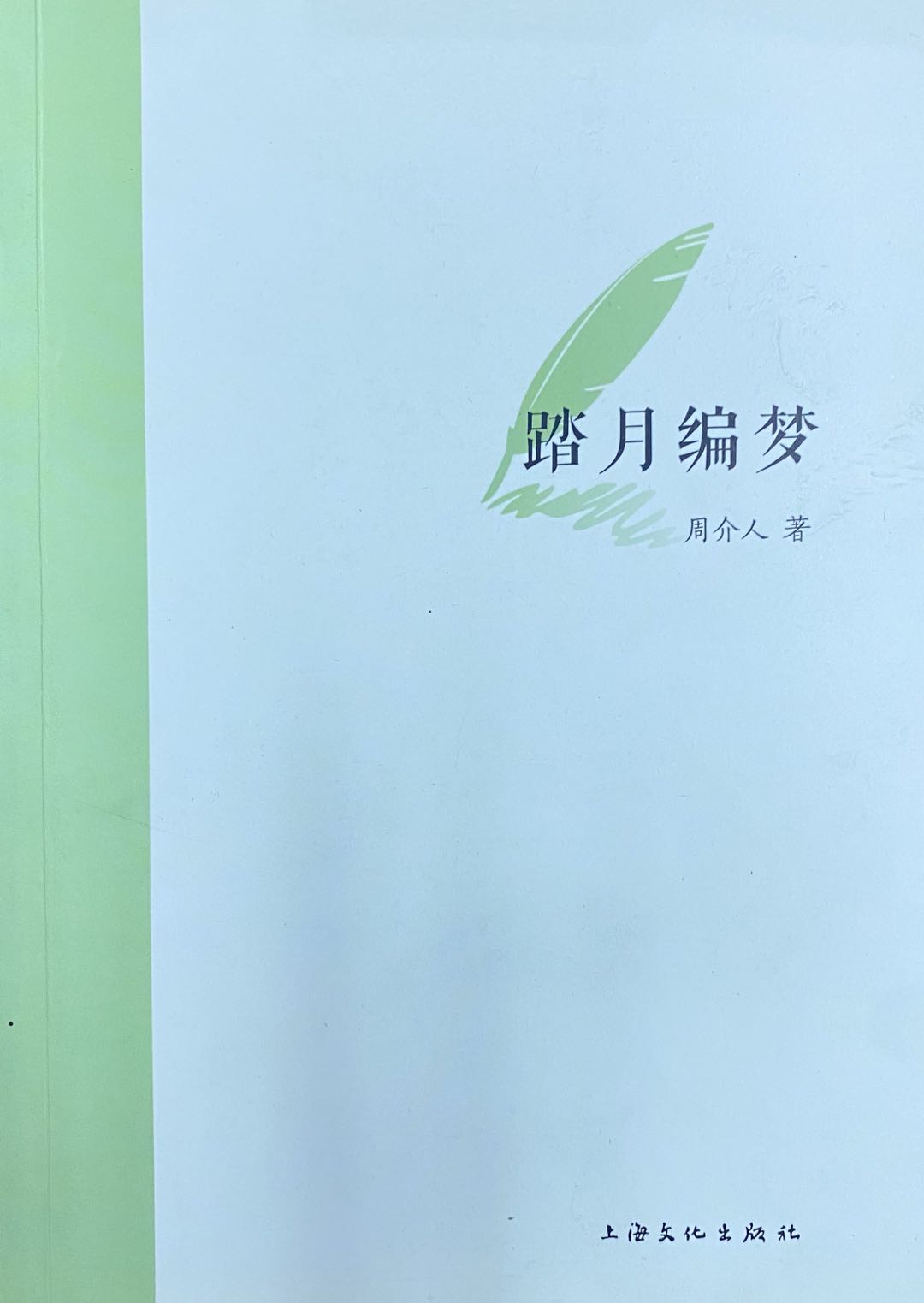
《踏月编梦》,周介人(著)
一个人如果停止了思考和探索,那他的生命价值会变得可疑。同样,一份文学杂志如果延宕了理想和创新,那她的精神蕴涵也将显现僵滞。历史已经证明,唯独因为凭借了开阔的思想视野以及考量现实的话语能力,二十年来《上海文学》才会始终独立文学潮头并且充满活力。不然,她将可能逐渐丧失自己的历史定位与个性品质,钝化自己介入现实的提问能力与思想锐气。这些年,周老师他思考问题时那头微微后仰的神情仿佛总在我们脑海间浮现,似乎催促着我们以及今天的《上海文学》务必紧密接续曾经由他传承而来的思想传统,这就是对历史的探询与追问,对于现实的介入于回答。
周老师的遽然去世,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哀痛和伤惋。而让我一直记得的是,在我最后一次到医院探望周老师时,他对我们年轻人因文学的不景气而产生的思想游移所轻轻流露出的责备与无奈。虽然,他一生坚持的文学理想备受时世的冲击,但他绝无沮丧,更不逃离,他把所有的委屈和酸楚留给了自己。而对我们来说,失去周老师的心痛感觉,还有他的文学沉思给予我们的启示,则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愈益强烈地感悟得到。是的,也许直到今天,我们终于有所明白。
于是,我们不由得深深怀念他——像这样为文学理想鞠躬尽瘁,尽付芳心的一个人。

 杨斌华,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编审。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上海作家》主编。著有评论集《文学:理解与还原》《旋入灵魂的磁场》《家园与异乡》等,主编或策划编选《守望灵魂》《守护民间》《上海味道》《思想的盛宴——城市文学讲坛讲演录》《几度风雨海上花》等近二十种。
杨斌华,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编审。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上海作家》主编。著有评论集《文学:理解与还原》《旋入灵魂的磁场》《家园与异乡》等,主编或策划编选《守望灵魂》《守护民间》《上海味道》《思想的盛宴——城市文学讲坛讲演录》《几度风雨海上花》等近二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