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很摩登,一百年前的上海就很摩登,大马路、霞飞路、静安寺路,多半会出现在今天书写上海的书里,然而上海还有着一个被叫做农村的地方,和一大群被称为农民的人,一百年前饱受压迫尝尽辛苦,他们所有的仅是农田、菜地和三两间茅草屋,更有灾年与荒年。或许他们从未进卡尔登戏院看过戏,去大光明电影院看过电影,去大新公司买过百货,又或者从未读过一页张爱玲的小说,但他们与上海、与这座城市不可分割。
一
一间窄小的茅草屋,靠用草绳绑着十多根毛竹杆、细木头作为支撑,周身杂乱的糊着黄泥,避的了些风,避的了些雨,逢到大风大雨,瞬间倒为狼藉。茅草屋向北有一片树林子,村里死了的人被埋在那里,大家见惯了,没人害怕。向南的空地上堆着一梱梱稻草垒成的稻草垛,垒到两米高的时候由边沿渐渐向内收,直到稻草垛远远看去像个大蘑菇。稻草垛向前有个河塘,每当太阳收走余晖,夜色下袭来些风,河塘边的野草便簌簌的响,谁家的狗也会叫两声。尽管1882年的上海已经亮起第一盏电灯,但在落后的农村只能偶尔点上一会儿豆油灯,唯有这黑暗中充满了一点希望的光,照亮他们的世界。

旧时罗泾农村景象(绘图:陆军)
这是1907年,这是1907年的罗泾,上海宝山的最北面,临着长江,与江苏咫尺相望。这方土地上的人们世世代代多以农业为生,虽然朴素勤劳,却没有丰厚的收成,那时候,那里只是一个个偏僻贫瘠的小乡村,少人问津,如同与世隔绝。
1907年,小妹出生在罗泾一户普通的农民家里。她有一个比她大三岁的哥哥,后来又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白天在地主家干农活,晚上在自家地里忙碌,由于在地主家的时间比较长,往往顾不上自家的地误了农时,一家人只能喝些薄粥啃些地瓜。
小妹十岁那年父母亲接连得了病,面色洞黄,附近中医看后说是黄病,开过药方子,叫了赶紧去抓药。然而那时能有东西填肚子已属不易,哪来的钱买药。父母亲说熬一熬吧,会好的。于是一天天过去,父亲爬不起床了,每天只能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母亲的双腿肿得像两根老树根,没法下地做农活,只能眼睁睁看着地里的野草越长越高。哥哥去了地主家帮工,九岁、七岁的弟弟和妹妹饿得皮包骨头,整天围着母亲哭:“娘,我肚子饿……”“娘,我要吃的……”
旧时农村的小女孩身上会裹条布裙,小妹不会,每天早上都由母亲为她裹上。那天早上母亲在床边与父亲轻声说过几句话,叹着气将搭在一张小椅子上的布裙像往日一样为小妹慢慢裹上,裹上后双手轻揉的又抚摸了几下布裙,拉了几下裙角,布裙显得平整起来。母亲望了望小妹,继而低下头望着布裙说:“娘要出去一会儿,你在家里陪着爹爹和弟弟妹妹。”
见母亲出去,小妹问父亲母亲要去哪里,父亲说母亲去找村里的李家老三了:“家里实在没有吃的了,只好让你出去帮人家做事,你娘去和人家说去了。”小妹听完父亲的话,心里又急又怕,转身搬了小椅子来到窗口,爬上小椅子,伏在窗口向外望:“娘,你晚点回来吧,你回来,就要把我送人家了。”小妹心里想。渐渐远处有了母亲的身影,越来越近,小妹吓得赤脚跑出家门,向河塘边上的野草地奔去。
母亲回来见不到小妹,四处找了起来:“小妹,你去哪里了,小妹,回来呀!”小妹卧在草窝里不敢喘一口气,好一会儿工夫,才让母亲从草窝里拉出身子。母亲拍去小妹身上的泥和草,说:“孩子,不是娘不疼你,实在是为了活命,没法想了,才叫你去帮工,你离开娘,娘有多心疼!”听完母亲的话,小妹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放声而哭。
天色黑沉下来。母亲牵着小妹的手回到屋里,折了一截野草做灯芯,放入小油灯,擦上洋火,屋子顿时有了微弱的光芒。母亲捋了捋小妹的头发,抚摸着她的头说:“孩子,要活下去,天总会亮的,我伲穷人会有出头的日子的。”
二
浏河属于太仓,在罗泾的西北方向,是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地方,虽然两地不算远,但陆路极为不便,1922年3月才有沪太公司全线通车了一条从上海到浏河的沪太线。那天小妹跟着李家老三一路走到浏河,她不知走了多久,要去哪里,只记得出发的时候天是亮着的,快到的时候天快黑了。李家老三指了指不远处,说是娘娘庙,过了娘娘庙就到了。果然,小妹走着走着见到一座庙,许多人在庙里烧香拜佛,再绕过几个高高的门楼,他们进了一户陌生人家的门。

旧时沪太路景象
是里外两进式的双层建筑,跨过大门是天井,右墙摆了一口盛满水的大水缸。向前是前厅,正中央悬着一块木头牌匾。再向前有个院子,靠左种了一棵桂花树,花开银白。最里面是厅堂,用一块制作精良的青石栏与院子相隔,上面雕着百鸟朝凤、福禄寿喜。高高的墙、黑黑的瓦,两侧一间又一间的屋子,小妹在院长里看得入神,忽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男人穿着红黑色相间马褂,生着一张粗糙发黑的四方脸,手握一个素面白铜水烟壶。李家老三弯下腰上前与他说了几句话,就转身对小妹说:“小妹,以后你就在这里做工了,要听话,我走了。”出门前母亲关照小妹许多在外胆子要大些的话,可这时,她拉着李家老三的衣角,不愿放开,李家老三望望她,松开她的手,独自走出了大门。
男人吸了一口烟,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斜眼瞟了一眼小妹,随即回了屋里。后来小妹知道,他就是自己的东家老爷,东家还有一个地主婆,一个小少爷,七个长工,十六个短工,和一百多亩地。厅堂里许多人正围着桌子吃晚饭,走了好久的路,小妹的肚子早已饿了,她低下头,忍不住咽了几下口水。正在这时,从屋里跑出一个大脸的女人,伸出一根粗圆的手指指着小妹厉声叫道:“小赤佬,有什么好看的,还不给我干活去!”小妹被这一声吓的不知如何是好,一个老佣人见了跑来拉了拉小妹的衣袖,对女人说:“太太,我这就带她剥花生去。”小妹随老佣人进了厨房,老佣人说那女人是地主婆,脾气差得很,嘱咐她以后一定要听话。小妹紧紧靠着老佣人,轻轻“噢”了一声。
东家吃完饭,天上升起了月亮。月亮下面有块云,云压的低,月光透过云,把院子和屋子照的支离破碎。五六岁的小少爷嘴上抹着油,嚷着嗓子喊娘点灯,地主婆就喊小妹:“小赤佬,叫你早点去点灯,怎么还不去,你耳朵聋了?”老佣人回了一声说马上来,转而对小妹说:“太太等的急,你跟了我来吧,以后学我的样。”老佣人从土灶上取过一盒洋火,带着小妹走入厅堂。厅堂南墙靠着一张案桌,两侧各摆设了一个花几。案桌上供着幅云母山水小插屏,花几上却没有花瓶,各放了一盏煤油灯。老佣人熟练地取下一盏灯上的玻璃灯罩,旋了几下灯头边上的旋钮,棉绳做的灯芯就向上伸长了一些,点上洋火,再盖上玻璃罩。“先点厅堂的,再点老爷太太的屋子。”老佣人边说,边与小妹由厅堂左侧的楼梯上了二楼。点完灯,小妹继续回了厨房剥花生。小妹年纪虽小,但剥花生对她来说并不难,左右两只手的手指同时捏住花生,用力一按便露出红色的花生仁,她只是难过,她担心自己,她想着第一天来没有一口饭吃,往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呢?
老佣人是浏河本地人,五十多岁的年纪,也是穷苦人家,早几年死了丈夫和两个孩子,经人介绍,孤零零一人寄身在东家家里做饭带小少爷。老佣人拿小妹当了自己的孩子,不仅教她做家务,还为小妹挑下不少重活,让小妹觉得在这冰冷的家里存着唯一的一丝温暖。可是老佣人有回无意间敲碎了地主婆装茶叶的瓷罐子,被地主婆喊人打伤了一只手后赶了出去,自此地主家几乎全部的家务都压在了小妹身上,从井里吊水、淘米、做饭、洗衣服、扫地、养猪、纺纱、筛米、倒马桶……东家见她人小,特地打了两只小洋桶,一只喂猪,一只吊水。由于水重,小妹拿不动,剧烈摇晃的水桶总是溅湿身上的衣服。每天早上要倒马桶,一天清晨,小妹拎着马桶跨出大门时,由于门槛高,马桶碰着门槛洒了一地,地主婆找管家让她清理干净后狠狠抽了她两鞭子,又饿了她一天饭。每天晚上要筛米,由于米筛重,小妹双手捧着米筛一个时辰下来便腰酸背痛、头昏眼花。有天晚上,东家老爷躺在厅堂的摇椅上吸水烟,粗着气对正在筛米的小妹说:“死过来,给我搥搥腿。”小妹跑来老爷身旁,跪下敲起腿来。老爷吸了一口烟,闭上了眼睛。小妹已累得眼皮像千金重的石头往下掉,一边搥腿,一边也闭上了眼睛,无意间头碰上老爷的腿,老爷猛地睁开眼睛,吸了一口烟,狠狠蹬了她一脚,把她踢飞在了地上。
匆匆四年过去,有人传话给母亲,说小妹在浏河被折磨得不像个人样了,母亲听了抛下手里的农活,顾不上穿草鞋,光着脚,忍着一路的疼痛跑去了地主家。地主婆见来了个光着脚皱巴巴的女人,说是小妹的母亲,要领小妹回家,扔下句:“你放心回去吧,你女儿在我家有吃有穿,我马上又要给她做新衣裳了”,便打发走了她。那天小妹正巧去地里给长工送饭,回来听说母亲来过,匆匆追出门,却已不见母亲的身影,垂着头呆呆立在了门口。地主婆说:“只要你不回去,我就给你做新衣服、新鞋子。”小妹望了她一眼,又垂下了头。见小妹不说话,她对管家使了个眼色,说:“给我看住这小丫头,别让她跑了,她要跑,就给我打!”
家里一位干农活的长工,这天偷偷塞给小妹两只玉米,对她说:“孩子,你快逃吧,另找个活路去。”小妹听着长工的话,双手颤抖着接过玉米,突然生出勇气来,将玉米放进身上布裙的口袋内,没有整理任何东西,她也没有东西可以整理,与长工道了别,拔腿往门外跑去,偏偏此时撞见外出归来的管家,“要跑,我要你的命!”小妹来不及闪躲,被管家右手抓起腰里的布裙带子,左手抓住脚,用力摔在地上。小妹的头撞上一块石头,嘴、鼻子涌出血,将地上染红一片。管家见闯了祸,怕出人命,抽身跑开了。小妹忍住疼痛,用布裙擦了擦脸上的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回家!”
三
东西二十里地,几条乡间小路连成回家的路。路两旁没有庄稼,一畦一畦荒地铺满了一片一片野草,野草下远远近近卧着一个一个坟包。野草绿中带着黄,黄中泛着绿,风吹来,绿色的叶子在坟包上闪出亮光。路边稀疏的柳条飞扬起来,纠缠交错在一起,像几条长蛇吐着舌头在追赶小妹。小妹拼命向前跑,披着头散着发,跑的跌跌撞撞,一个脚软,摔在地上,脸上的血迹和泪痕又蒙上了一层土灰,爬起身,继续跑。当她喘着粗气推开家门的时候,空荡荡的屋里,只有父亲在床上奄奄一息地躺着。

(绘图:陆军)
“是谁呀?”小妹耳旁传来虚弱的声音。
“爹爹,是我呀!”小妹快步奔到床前“哇”一声哭了起来。
父亲睁开眼睛,望着小妹,抖动着干裂的嘴唇说:“小妹,你可回来了,给——给我一点吃的吧。”小妹从布裙里取出玉米,双手送到父亲面前:“爹爹,你吃吧。”父亲看了看,摇头说:“太硬了,我咽不下去,你有没有从东家带蒸米糕来?”小妹听完父亲的话,哭声愈加大了:“糕?对不起爹爹,没有。你看我头上还留着血。”父亲看着小妹,似乎明白了一切,心痛的不再说话了。
隔壁一位大娘听见声响走了进来,见小妹回来,走到床边扶起跪着的小妹,用自己的衣袖为她抹了抹脸上的血迹和泪痕。小妹抱住大娘,抽搐着身子问:“大娘,我娘呢?我弟弟妹妹呢?”“小妹,你可知道,你哥哥已经做活累死了,你妹妹饿死了,你娘拖着病带着小弟出去要饭去了,你爹躺在床上动不得,这日子你以后怎么过呀。”大娘说。
家,小妹满心期待的家,现在已家破人亡,死的死,病的病,除了一间破草屋,缸里没有一粒米,灶里没有一根柴,这还是家吗?
第二天早上,小妹沿着家附近的一条小河没有目的向南走。不知不觉,下午走到了新镇。
罗泾的南面是月浦镇,两地相接的地方最初不过三四间茅草屋,因有一条河,有僧人集资在河上建了一座桥、河边建了一座庙,渐渐多了人家,又有了小木行、布庄、药铺、茶酒店……有人就将这热闹的市集叫作了新镇。

旧时月浦街景
一户人家门口,有位三十来岁的女人见小妹心神不宁地走着,问她要去哪里,小妹望着女人,一肚子的酸楚涌上心头,向她吐露起自己的种种遭遇来,女人听后说:“到我家来做工吧,一个月四十个铜板,你愿意就留下。”“我答应。”小妹露出难得的笑容。然而一个月很快过去,东家没有给小妹一个工钱,对小妹说:“我先给你保存着,你继续做,等你要走了我便给你。”小妹信以为真,当四个月过去,她以为自己存下一百六十个铜板可以回家给父亲治病的时候,东家反而骂起了小妹:“小赤佬,你弄丢了家里一把小刀,算你白做了四个月了。”小妹觉得冤枉,却毫无办法。
几天后,东家隔壁来了两个客人,在新镇闲逛时见小妹在河边洗衣服,手脚利索,衣服洗得干净,上前问她是哪家的姑娘,小妹说是罗泾的,在新镇做工:“上海有人家每月能出一百五十个铜板,你愿意去,我们明天在浏河等你。”来人说。小妹听了高兴,想着能用一百五十个铜板为父亲治病,便匆匆洗完衣服,回东家辞了职,东家没有挽留,给了她几个铜板随她离开。傍晚时分,小妹到家见了父母亲,说要去上海做工,母亲说好,正要出门,天突然下起大雨。家里没有伞,母亲说等一会儿再走吧,小妹怕错过做工的机会,和父母亲道了别,随即冲进雨里。母亲拿了自己一件衣裳,追上小妹,把衣裳披在女儿身上。小妹看看母亲,点了点头,走了。走出一段路,小妹回头望望,母亲依旧站在家门口,小妹擦了擦掉入眼睛的雨水,转过身,在泥泞的路上,向浏河走去。
四
新东家姓滕,是开纱厂的,住在新闸路一幢五开间的两层石库门里。家里有一个母亲、大小两个太太和一个小少爷。每天天不亮,东家仍在熟睡时,随着粪车隆隆而来,小妹拎着马桶推开那扇黑漆的铜环大门,一天的劳作开始了:洗被子、洗一家人的衣服、做饭……直忙到晚上东家一家人睡熟,才能休息。每天小妹伺候老奶奶吃过早饭,老奶奶便把自己关在一楼靠东墙的佛堂里念佛,下午或晚上由大太太陪着去戏园子听戏。小少爷是大太太生的,老奶奶说,家里的一切都得听大太太的安排。大太太爱挑剔,常嫌小妹煮的菜太咸,洗的衣服不干净,对小少爷不亲,常常便对着小妹扯头发、掐手臂。二太太是老爷买来的小妾,有着当电影明星的野心,右手拿着纸烟,时不时叼在嘴里的样子倒真像美丽牌香烟盒上的模特,可是老爷关照大太太对她管得紧,不让她出门,二太太心里有怨,把气全撒在了下人身上。照例每周三天的下午她约了人在家里打牌,那天输了牌见小妹正在洗衣服,把手里未吸尽的一支烟扔进洗衣服的木盆里,接着一脚踢在木盆上,不想踢疼自己的脚,愈加来气,端起木盆,把盆里的脏水、衣服和烟倒在了小妹身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文化已涌入上海,对上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服饰文化同样有了许多改变和升华。这是小妹第一次在上海做工,老爷的洋装,配上锃亮的皮鞋,老奶奶、两个太太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旗袍、大衣,看得小妹眼花缭乱,然而小妹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布衣服,和母亲给她的那件衣裳,东家没为小妹添过衣服,小妹只能把这两件仅有的衣服穿得小心翼翼,脏了自己搓搓,破了哪里扯块碎布自己补补。天气暖和时都能应付,冬天却难熬了,这单薄的衣服哪能抵挡刺骨的寒风,刷马桶时冻得发麻的身体除了忍受刺鼻的气味,握不住马桶刷的两只手不得不轮流放进嘴里、放在额头上或伸进脖子里取暖,手指头、脚趾头满是疮,哪怕她不停的在地上像只跳蚤一般的跃起。
房子的顶上有个阁楼,需要借助一架梯子才能爬的上去。东家把阁楼修成了大小两个空间,中间用木板隔着。大的堆满了皮箱子、木箱子,小的仅容得下两三人躺下,没有任何家俱,成了夜晚小妹躲避这世间苦难唯一的地方。与她最亲的是地板上铺着的那张草席,和草席上垫着的那张因使用久远而磨去了花纹的棉花毯子,那是她的床。屋顶有一扇老虎窗,每次睡下,小妹透过老虎窗看得到窗外的星星,望着星星,她总想起母亲的话,她想问母亲:“娘,天真的会亮吗?我伲穷人真的会有出头的日子吗?”
两年下来,有天早上小妹迟迟没有起身,大太太以为她偷懒,叫了人要把她吊起来打,去的人却见她瘫在阁楼上不能动弹,说不出话了,大太太觉得这臭丫头怕是要死了,万一死在家里晦气,不想惹麻烦,便叫人拿了些棺材钱,派人将小妹送回了罗泾。
母亲见女儿已病得半死不活,人瘦得像根木柴,脸黄得像张腊纸,眼睛深深凹陷的像具骷髅,抱着她的手不舍得放开。邻居见小妹神志不清,明明点着灯,嘴里却喊母亲要点灯,明明母亲在跟前,却视而不见,就催母亲赶紧去买具棺材,准备后事了。母亲不肯,说:“女儿要死了?我不信,如果她死了,我也不活了,这点棺材钱,我给她买药……”就这样,靠着母亲熬尽心血日夜照顾,小妹竟死里逃生,活了下来。
小妹的舅舅日后送小妹陆续到上海的几户人家去做过丫头,算起来自小妹十岁出门,前后在十二户人家帮过工,也去闸北的纱厂做过工,尝尽人间的辛酸,最后因为脚上生疮行动不便,回到了家里。回来的那天,她在路上捡到一个铜板,换了两只酸梅子充饥,含着酸梅子,她看着自己身上的破衣服,离家时穿着它,回来时依然如此,只是更破了,原来自己一无所有。
五
罗泾有句俗语,“螃蟹剪草海滩田,海龙王作对大荒年”,意思是海滩田不会有多少收成,碰上江水淹了庄稼,只能颗粒无收。因为宝山地处海滨,境区有百多公里岸线襟江带海,每年夏秋之际,常因台风、暴雨等侵袭造成严重的灾害,引起大饥荒,需要依赖官府的赈粥济贫,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小妹二十一岁那年,经了村里人介绍,嫁去本地一户张姓人家做了媳妇,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弟弟外出当了学徒,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小妹和丈夫一起种着海滩田艰难度日,第二年她们有了一个儿子,接着有了两个女儿。小妹是吃过苦的人,她不怕苦,只希望太平的过些日子。
1937年8月13日凌晨,村里养鸭的阿兴去江堤旁给鸭子捉饲料,见停在长江上的日本军舰发射了照明弹和炮弹,踉跄着一脚踩在湿滑的草上摔了一跤,爬起身匆忙往回跑,高喊着:“东洋人打来啦!东洋人打来啦!”没跑多远,阿兴被日军开枪击中,死在了江边。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准备,守卫在罗泾沿江的中国军队只有一连兵力,且分散在石洞口至薛泾塘约十几里长的江岸线上,面对日军从罗泾南石洞口附近的黄窑湾、中部小川沙港和北面薛泾塘三处发起的大兵团登陆进攻,虽然进行了抵抗和反击,终究寡不敌众,很快全部壮烈牺牲。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登陆处:罗泾小川沙滩地
日军上岸后,一把火点着了紧挨着江边的宅子,十多户人家几十间房屋被烧成一片火海,侥幸从火海中逃出的百姓,四处逃散着告诉乡亲们快跑,小妹与丈夫慌乱中一人挑一个担,装着锅子、碗、被子,后面跟着年迈的婆婆和三个孩子,一路向西逃去。
两天后,小妹一家到了无锡,在无锡南门外,小妹的丈夫打算寻些柴草铺在地上过夜。走过一座砖瓦窑时,遇上六七个国民党自卫队,不由分说把小妹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他倒在地上没了动静,才扬长而去。
丈夫许久不回来,小妹安顿下婆婆和孩子外出寻找,没想见到自己的亲人倒在血泊之中。小妹跪在丈夫身旁,呼唤着他的名字。过了好一会儿,丈夫苏醒过来,低沉着声音说:“不要紧,我还活着,当时我只要再哼一声,这些强盗就打死我了。”小妹把他从地上慢慢扶起,一气背着他走了好几里路,找到一间荒废的老祠堂。推开破旧的木门,院里的草已没了人的膝盖,墙边靠着几架木头开裂的农具,正中间摆着十多具棺材,棺材前方有个案桌,案桌上的香炉里洒落着半炉香灰,边上凝固着一摊蜡油,竖着的几块牌位和几个丑陋的泥塑鬼神逼的人一身寒气。小妹大着胆子拼起两具棺材,铺了些柴草,与丈夫睡了一夜。第二天小妹怕丈夫被当作伤兵捉去,让他躲在祠堂附近的河沟里,自己接上婆婆和孩子去要了些饭,待到天黑,继续住在了祠堂里。小妹的丈夫说:“以后要让咱儿子也去当兵。”小妹说:“不,也要他拿枪去欺负人?”“我要他去当个好兵,去杀日本鬼子,去打坏人打土匪!——儿子,以后也去当兵好吗?”
11月23日,小妹一家人从常州回到罗泾,然而眼前的罗泾已面目全非,房子被烧光了,地里的庄稼被烧焦了,死了二千多人,回来的乡亲,人人在惊恐和饥饿中数着日子。日本人上岸时,小妹的母亲收拾了东西正准备逃走,一颗炮弹突然掉下来,炸伤了她的脚,没法走路。没有药,伤口渐渐溃烂,生了许多小虫,母亲只得将脚浸在水桶里。开始有人给她送些东西,渐渐村里人逃光了,母亲便强忍着疼痛,找来四块砖头,上面搁一块木板,躺在稻田里,靠两个青南瓜充饥。不久扫荡的日军在稻田里发现了母亲,将她一刀刺死,直到小妹回来收尸,她身边还留着半个没吃完的青南瓜。小妹说,这血海深愁,一辈子忘不了。

被日军摧毁的罗泾民宅
小妹和丈夫搭了一个草棚算作安身之所,为了生活,不得不一人种地,一人接着外出要饭。也许过于劳累,地里的庄稼在渐渐生长,丈夫的伤口却时时在作痛,有时大口大口的吐血,勉强支撑了五年病死了。临死前,他知道小妹的日子会更难熬,对小妹说:“家中没有东西了,对不起,我死后要让儿子去当兵,女儿去做童养媳吧。”
小妹的日子的确更为难熬,婆婆和三个孩子全靠她一人照顾,生活的重担压的她喘不过气来。那些日子,天上下雨,她要去地里,天黑了,她要去地里,逢到春耕插秧,就在田头住半个月,不过日子再苦,她依然相信过去母亲对她说的那句话:“孩子,要活下去,天总会亮的,我伲穷人会有出头的日子的。”
六
1945年8月,那天午后,大太阳底下,小妹正在地里摘黄瓜,一块蓝色土布包裹着她的头发,额头是一滴滴的汗。儿子跑来地里,告诉她日本人投降了,小妹听了停下手,问:“真的?”儿子答:“真的。村里人说报纸上都登了。”小妹让儿子回去,独自跑去了母亲坟上。
过了几天儿子又对她说,村里有人给他在吴淞的永安纱厂找了事做,他要去吴淞。小妹在纱厂做过工,知道纱厂做工的艰辛和“拿摩温”的狠毒,本不希望儿子去,但想着日本人投了降,纱厂不会欺负人了,也就同意。然而儿子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她曾托人去吴淞时打听过几次,却毫无音信,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儿子已经遭遇不幸。
1949年5月解放军攻打上海,5月12日夜里到达月浦后向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攻击。那几天小妹坐立不安,没心思下地,守在家里时不时望着月浦方向的炮弹一次次爆炸后升腾起的火光把天上照得又红又亮。村里人说月浦快烧光了,老街都打烂了,小妹听了害怕,但十多天后战火平息,村里人又个个笑着说解放军打跑了国民党,上海解放了,满大街飘着红旗,是共产党来了,我们的好日子来了。

解放军到达月浦后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

上海解放后宝山各界在街头进行庆祝活动
一个月后,有位年轻的解放军来村子找小妹,村里人将他领到小妹家里。小妹问他是谁,他说是小妹儿子的战友,原来小妹的儿子在攻打上海时牺牲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团3000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几十人。他之前给了我地址,我答应他,如果我活着,一定替他来看看你。”解放军说。
由于部队刚进上海任务重,解放军呆了没多久,便向小妹道了别。待他走后,小妹默不作声,独自坐在了窗前。渐渐的天黑了,和家人吃了些东西就睡了。天快亮的时候,她怎么也睡不着,起身披上件衣裳又坐向窗前。窗外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漫天飞舞,一会儿落向草丛,一会儿扑向树丛,一会儿又飞向小妹,落在她的脸上。年过四十的小妹,黝黑瘦小的脸上被生活雕琢出的那一道道皱纹此时愈显深刻,像糊在草屋身上那些干裂的黄泥,俨然六七十岁的老人。
“儿子是个兵了,是个不欺负人的兵。”她喃喃自语。不一会儿,黎明在小妹的眼前,慢慢升起。





今日罗泾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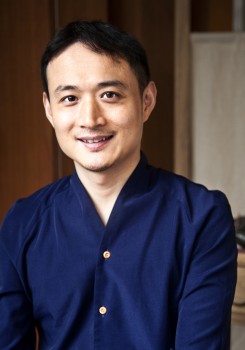 唐吉慧,上海宝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宝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济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等。著有散文集《旧时月色》《旧时相识》,编著有《俞振飞书信集》《周有光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集》《陈伯吹书信集》等。著作入围上海40年优秀文史类图书,并获上海市作家协会年度作品奖、冰心散文奖优秀奖,及《文汇报》上海文化新人等。近二十年致力于近现代学者作家手迹、文献的收集挖掘整理工作,策划有周有光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多党合作制度确立70周年——文心灿烂·中国近现代学人手迹展。
唐吉慧,上海宝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宝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济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等。著有散文集《旧时月色》《旧时相识》,编著有《俞振飞书信集》《周有光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集》《陈伯吹书信集》等。著作入围上海40年优秀文史类图书,并获上海市作家协会年度作品奖、冰心散文奖优秀奖,及《文汇报》上海文化新人等。近二十年致力于近现代学者作家手迹、文献的收集挖掘整理工作,策划有周有光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多党合作制度确立70周年——文心灿烂·中国近现代学人手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