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生肖》演出进行时 上海杂技团供图
一位法国商人的“上海忧虑”
2013年的9月,刚下过雨的上海,空气粘稠。一位住在上海的法国人,望着窗外近在咫尺的上海马戏城,额头上也是一片“粘稠”。两个月后,已经签约的上海马戏团,将赴巴黎演出。在上海举行的项目“验收”会议上,这位法国人说:“我非常渴望能在巴黎呈现一台代表上海水平和现代马戏的晚会,”随着话锋一转:“巴黎不是上海。”结束语非常严肃:“我想讲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上海方面的回答是:“我们会举全团之力做好这次合作。”。
这位法国人名叫阿兰·巴士里,身份是法国演出商巨头。上海作回答的,是上海杂技团团长、上海马戏城有限公司总经理俞亦纲。
每年秋冬,当雪花飘落,炉火腾起,圣诞钟声临近,整个欧洲延续百年之久的秋冬“马戏演出季”就开始了。巴黎是演出重镇,从岁尾的11月中旬至次年1月,有十几台大型表演秀在巴黎郊外Vincennes森林安营扎寨,个个有备而来,家家奇招迭出。其中,法国演出与大型活动公司麾下的凤凰马戏推出的杂技晚会,是全城瞩目的焦点。
法国“演出和大型活动公司”全称为SOCIETE DE SPECTACLES & EVENEMENTS,作为品牌演出公司,其经济实力和市场份额占有力在法国业内雄踞榜首。“杂技晚会”先在世界最大马戏棚,能容纳五千多为观众的凤凰马戏棚里演出,随后在法国及瑞士、比利时作巡演。年近七旬的阿兰·巴士里的口头禅是:“在巴黎,人家不来看你的演出,这日子就过不下去。”
应允合作的俞亦纲心里明白:即将参加赴法演出剧组的大部分演员,是从沪西文化宫驻场演出团队中调来的。这个既是“团”又是“宫”的演出组合,其演出和经营似在给人一种“机制混杂”的印象。俞亦纲面对两个难题:一,当下演出队伍缺乏国际舞台演出经验,根据合约,在巴黎演出两个多月,共计70多场,接下来要在全法境内和欧洲法语区巡演,体力强度很高,很难预料不出现“情况”。说得容易,希望全体演员在异国现场迅速成长、成熟起来。但这事情想起来就有点玄乎,上海的苗,移植到欧洲的地里,还要茁壮成长,谁能作这个保证?二,以往与外方的合作,上海杂技团只要按部就班地上奉献“绝活”就行,演一场挣一场的演出费,类似摊贩出货,卖掉一件是一件。这次“与国际接轨”,上海杂技团与法方公司共同制订商业演出方案,其中包括重新设计节目,连演两个多月,那就是“大中型企业批量化的订单生产”;在经济收益方面,中方拿商谈好的固定酬劳,且这份收益的数额,超过了以往到法国参加演出的中方杂技团收入上限,这无疑是在表示法方的姿态:我们已经开出最高的“收购价格”,且看中国人将以怎样的姿态来提升“走红毯”的眼球效应。
第一个是人的问题,第二个是钱的问题。法国商人的额头“粘稠”,滴沥着汗水,是有原因的。
从黄金地段到“荒凉乡下”
上海杂技团的瘫痪,在那个辽远的“文革”年代,是当然的事情。
1971年,为准备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以及美国尼克松总统,周恩来总理直接指示,上海人民杂技团恢复正常排练。下一年的2月,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华的美国总统夫妇观看上海杂技团的专场演出。那个日子,后来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这话的口气说得太大了,杂技表演哪有改变世界的功能?事实是,小小杂技团的命运被世界改变了。具体地说,就是上海杂技团借此开启了中断多年的招生,以扭转杂技人才几近断流的颓势。

所谓“招生”,是到全市各所小学去“看”去挑。在教室里,安排一群孩子做游戏,首先看长相俊不俊俏,讨不讨喜欢,这决定了以后站到舞台上有没有“观众缘”。其次是看身材,也就是看形体和骨架,主要看手脚骨骼的线条直不直。第三看机变能力,也就是“胆子加灵敏度加判断力”。
从上海的10个区、10个县挑来60个学生,男女各半,最大的12岁,最小的8岁,组成一个训练班。后来当上了副团长的蔡荣华,当年是静安区一小的孩子,才刚满11岁。1972年10月,孩子们走进新华路的上海杂技训练班,过上新的集体生活,也早早尝到了练功的艰辛。在孩子记忆中,天天有人“吃生活”,也就是吃苦头。“练功苦,老师凶”,谁“偷懒”就可能在屁股上挨上一下,俗称“竹笋烤肉”。训练房里,不时地会从角落里传出小孩的哭声。一年多过去,班里就有3个身体条件不错的孩子,被家长坚决地领回去了。
手脚受伤是家常便饭。去医院打个石膏,回来照常训练,手坏了练脚,脚坏练手,左手坏了练右手。蔡荣华就曾经手腕骨折,后来又脚腕骨折。他不想让家人担心,星期天父母来看望,他先把石膏拆掉,等家人走了再给自己绑上。
时光艰难,经岁月雕琢的这些孩子,到了能够上台演出的时候,恰逢“文革”结束。付出有了回报。蔡荣华“刚上班”的工资是36元人民币,比工厂学徒的要高多了。他第一个月领工资,与全家人的收入凑在一起,买了台红梅牌12寸黑白电视机。在邻居的羡慕中,蔡荣华感到一份“经受风雨就有彩虹”的满足。更为旁人羡慕,是作为当时“中国文艺界标志之一”的杂技团,经常有机会出国演出。在当年的年轻演员眼里,这是“一份相当大的福利”,挣外币,买洋货,那是“上海人再有钞票也没法买到的原装进口货啊”。
1980年,上海杂技团首赴美国纽约等6个城市商演,开中国文艺团体出国商演之先河。第二年,上海杂技团组织 70人东渡日本巡演4个半月,走了20多个城市,从最南的冲绳到最北的北海道。这次日本之行,蔡荣华带回一台三洋牌14寸彩色电视机。团里几乎人人都采购了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托运回上海。
经多次出国演出,家里进口电器也渐渐配齐,1986年,蔡荣华再度赴日演出4个半个月,买回来一台全上海罕见的踏板摩托车。他骑车上下班,被一交警拦住,为的是看一下这辆“豪”车。那时,一个杂技演员在日本演出一天的生活费是6000日币,折算成人民币,相当于当年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
出国演出让演员个人尝到甜头,也为杂技团的后续发展迎来了活水。1988年,中国第一所培养杂技人才的专业学校上海马戏学校诞生,启动资金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杂技团出国商演挣下的外汇。
老上海人都记得南京西路上又名“风雷剧场”的上海杂技场。这座大型圆顶建筑,每晚的大型霓虹灯招牌吸引着来往行人。大凡国家元首、政界要人莅沪访问,必到此观看杂技晚会。到杂技场此看杂技,去豫园吃小笼、淮海路买皮鞋,成为了抵沪游客的“标配”。

那是上海杂技人怀念的黄金时代。“那时生意真好,周边黄牛都靠我们发财”。偶尔,关在杂技场后面兽笼里的马戏动物“伺机越狱”,猴子翻窗,小狗翻墙,甚至曾有一只老虎冲出兽笼,幸亏及时捉回,要不就“流窜”到南京路上去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演出界迎来的是“名利双收”的黄金岁月,演员们迎来自己的第一个艺术高峰。
1984年,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在兰州举行,上海的《大跳板》获总分第三。同年,同类型节目《跳板蹬人》参加第十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获得摩纳哥城市奖。1987年,第二届全国杂技比赛在上海举行,上海杂技团囊括了杂技、驯兽、魔术三项第一,《大跳板》获得金奖,成为上海杂技团的保留节目。
饺子再好,也不能顿顿吃,好日子总有到头的一天。90年代,市场经济激活了千姿百态的文艺演出,杂技表演的“老一套”光彩寥落,在最凄冷的时候,风雷剧场租给了商家,成为卖羊毛衫的铺面。“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1995年,这座著名的地标式建筑被拆除了。
上海杂技团整建制北迁到闸北区的共和新路。搬家后,杂技团面临的是“荒凉乡下”。“那时一号线还没有延伸段,高架也没架到这里,夜里一片漆黑,一星期只在双休日演出两场”。
“苦练”两字不再是唯一台阶
上海杂技人在经历阵痛,外面世界的同行们也不安宁。如何走出“套路”,赢得新的掌声和票房,是同一难题。
在平行的时间段里,1974年,摩纳哥大公雷尼埃三世创办了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秉承欧洲古老传统的杂技马戏血统,迄今依然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杂技艺术节。1977年,法国演出与大型活动公司创办“明日”世界马戏节,该节每年1月下旬在“凤凰马戏棚”举行。“明日”马戏节以“艺术审美”为首席标准,奖掖节目编排,鼓励马戏艺术呈现多样化,这被约定俗成地称为“新马戏风格”;并坚决摒弃动物保护人士反感的驯兽类节目。如是,在杂技马戏业的躯壳里,有“传统”与“明日”两颗心脏在同时跳动。
1984年,也就是上海杂技团的《大跳板》获得国内第三名而不甘心的这一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两个街头艺人,创办了一家娱乐公司,起名叫索拉奇艺坊。凭借“马戏艺术和街头娱乐颠覆性的戏剧性组合”,所到之处引起潮水般的轰动。富有蓬勃生命力的演出被称作“太阳马戏”。
太阳马戏是欧洲“明日”风格的杰出代表,后来到上海杂技团来洽谈业务的法国人阿兰·巴士里,就是明日马戏节的评委会主席。这位年近七十的巨商,自身麾下的凤凰马戏,当然也属“太阳风格”。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太阳马戏融歌剧、花样游泳、马戏、魔术、芭蕾等艺术形式于一体,还是马戏的那些技巧,还是杂技的那些手法,技术难度并不高,然而场面大,演出效果惊人。与太阳马戏节签约的80多个国家的杂技演员,内中不乏华人,内中就有飘洋过海来讨生活的前国内院团演员。
经历了十多年摇摇晃晃的日子,在新世纪初,俞亦纲出国考察。耳闻不如眼见,他被“太阳马戏”的火爆而震撼。太阳马戏有很多著名作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奢华酒店百丽宫驻场演出的《O》秀,票价近两百美元,场场爆满,头几排位子还要提前几个星期预订。《O》秀从头到尾没几句台词,依靠肢体语言,将剧情演绎得天衣无缝。演员表演精确到位,舞台设计、音乐声效、桥段处理,旨在体现人类幻想的恢弘与壮丽。太阳马戏具有“灵魂魅力”,时而流露出对小人物的同情,充分表达一个小丑含泪的笑,时而描摹爱情的绝望,让天空巨大的船只为之燃烧毁灭。
如何让杂技马戏给人看出丝丝缕缕的哀伤,这是中国杂技界从来没有设置过的“课程”。
中国杂技难度高,给观众观感最大的震撼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这样演出形态,当属传统范畴内的最优秀作品。脚下已是新的世纪,俞亦纲明白,全球杂技业界同时跳动着两颗心脏,那就意味自己的道路只能是:老牌竞技不可放弃,潮流涌现亟待跟进;既要立足国内,更要走向世界,国际演出市场对“新马戏”的青睐,这决定了上海杂技团再不能躺在旧的表演套路上睡大觉,“我们的演出观念和美学境界已经落后了,我们还在苦练,人家已经巧练”。
团长俞亦纲在咀嚼“方向”,当了24年演员的副团长蔡荣华考虑的是“出路”。

钢丝独轮车——羚羊 吴越 摄影
杂技演员的台上生涯,非常短暂。“如果一直以‘难’字挂帅,中国杂技的发展肯定萎缩。杂技这个行当,对人的身心是有影响的。一些演员身体有伤,女演员练蹬人节目,个别动作需要蹬到肚子,这样的10年下来,会妨碍正常生育的。类似的节目、技巧,必须淘汰。还有,因为一成不变,再难的节目人家也会看腻。没有故事,没有新的内涵,就是个天桥卖艺的形态,有谁再愿意买单?”
“苦练”两字,曾经是荣誉和成功的基石,概括了中国杂技节的昨天;而当下,它却不再是艺术和效益的唯一台阶。
创造“上海水平的现代马戏”
年轻时的俞亦纲是一名空军地勤兵。这段职业经历让他惯于打量飞在天上的事物,他也知道,“遥远”并非不可抵达。
考察回国的俞亦纲,当然地感到了距离。曾有人说,中国杂技就像遍布长三角、珠三角的外贸工厂,给人家贴牌制造产品一样,中国杂技演出队跑遍世界,挣的也就是一点“made in China”的演出血汗钱。这还是好的,俟世情世风更变,人家演出内核的寓意已经远远递进,观众欣赏口味大大改变,中国杂技“过硬”的技巧,居然已经无牌可贴。2005年,三思而行的他,主动向上级主管单位SMG即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提出改革建议;然后北上首都,“联络”文化部所属的对外演出公司——中演公司,陈情现实利弊和可能的前途之路,三方组建项目公司,启动资金是向银行借贷1000万元人民币。
跻身在新旧之间,上海杂技团派员远涉重洋,引进加拿大“太阳马戏”班底中的几位外籍编导,来策划崭新节目的结构框架。这个后来命名为《时空之旅》的演出,从一开始,就往中国传统杂技的血液里注入了“太阳马戏”的基因。
《时空之旅》在2005年首演。形式也是内容,这是头一次。在演出票面上,《时空之旅》前面的定语,既没有杂技,更没有马戏,被冠以了“多媒体梦幻剧”的名称。在广告牌上,这台节目就用了一个“秀”字来概括。这是上海杂技团第一次启用“秀”的概念:“秀一个上海给世界看”。卸下“卖艺”的面目,“报幕—挨个表演—谢幕”的舞台流程从此隐身。整台演出用讲故事的形式,融杂技、舞蹈、戏剧、音乐和多媒体技术于一身,采用声光电技术,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观赏冲击。
《时空之旅》每晚在上海马戏城准时开演。从2005年首演至2013年9月,演出票房收入突破4亿元人民币。《时空之旅》的横空出世,成为一个艺术创新话题,更是一个市场经营话题,成为上海新闻媒体和文化节的关注焦点。
资本嗅觉具有这个世界最高的灵敏度。上海同行的成功,引得巴黎商人闻讯而来。
自1994年起,经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处牵线,法国演出和大型活动公司开始了与中国杂技界的合作。法国公司每两年在本土秋冬的“马戏演出季”里,举行一台中国杂技晚会的演出。15年来,已有中国沈阳杂技团、广州杂技团等6台节目,在“世界最大的,能容纳五千多为观众的凤凰马戏棚里”上演。法方与上海杂技团签约,共同创排中文名《十二生肖》的全新节目,到时参演。

阿兰·巴士里在演出开场前热情洋溢地致欢迎词 吴越 摄影
这是中国杂技团赴巴黎演出的第7台杂技节目。
凤凰马戏的节目制作,要求灵活而严格。每年,它在世界范围内遴选顶尖杂技团作为“舞伴”,再共同原创一台既具异域色彩而又符合法国口味的舞台秀。凤凰马戏曾与墨西哥马戏团制作的是“雨林历险”,与俄罗斯冰上杂技团推出的是“冰雪传说”。节目成型,凤凰马戏的广告片,就会滚动式地通过各种媒介渠道,反复播放,拽着人们掏钱买票。一年一新,常变常新,这是凤凰马戏半个多世纪来立于不败之地的铁律。
十二生肖是中华“国粹”,外国人不明白这十二个动物与人类有什么血脉关系。所谓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彼此的不同,也就是区别。在文化区别中缔造人类经验的通感,这就是艺术的使命,也是商业收益的命脉。法国商人阿兰·巴士里深谐其中奥秘,为便于高傲巴黎人的理解和感受,在广告的图文介绍中,他把神秘东方符号的“十二生肖”与欧洲文化语境下的“十二星座”,捏和在一起,从而搭建一座商业演出抵达双赢彼岸的桥梁。
参加2013年凤凰马戏秋冬季汇演的,将有16个国家的杂技团,其中就有加拿大“太阳马戏”剧组,上海杂技团中标“主打演出”,这就明摆着,上海与“太阳”有一场近在咫尺的针锋相对的竞争。这是阿兰·巴士里的一次冒险。阿兰·巴士里在上海的工作会谈,他总是先以欧式的口吻表示问候,紧接着就用“那一张扑克脸”进行毫不客套的细节追问。一轮会谈讨论几百个细节,小至道具用铝合金原色还是漆成黑色,某段开场音乐用唢呐还是用鼓,大至节目排序、人员增减,等等、等等。法国人一丝不苟,亲力亲为。而在每一轮会谈结束时候,他的结语又会恢复含蓄的欧式期待:我非常渴望能在巴黎呈现一台代表上海水平的现代马戏晚会。
俞亦纲当然听懂了这句话:上海水平,现代马戏,水乳融合也好,硬件焊接也罢,“法国老板就等着看上海人的脑子怎样转动了”。
从“震住别人”到“感染观众”
冲撞和协调无处不在。
上海设计的开场白,即遭法方否定。《十二生肖》创排阶段,剧组精心准备了一段长达6分钟的“亮相”,这源自中国式的惯性思维,朋友相逢,行礼招呼,寒暄暖场。欧式舞台上的演绎,没那么繁琐的铺排,在预演合成阶段,法方将之删减到只有1分钟。“法国人认为,一台好的演出,一开场就要立即抓住观众的兴奋感,迅速进入主题。中西文化有差异,无优劣,关键是要看这一场演出面对的是什么观众”。
与亮相的时间减缩相反,谢幕的时间则大大加长。剧组习以为常的谢幕形式,遭到阿兰·巴士里拒绝:不要走动,不要鞠躬,不要挥手,不要抱拳,不要有人“领掌”,不要“板脸”,更不要摆阵型;要的是“原位微笑5分钟”。
上海杂技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赵雪把阿兰·巴士里归纳出来的上述几个“不要”,一条一条地翻译成中文,但她一时并不明白为什么“不要”。舞台监督陈姝苗发现,这最后5分钟的法式谢幕,站着纹丝不动,并非易事。无论观众怎么鼓掌,演员站在自己最后的演出位置上,眼睛平静而自信地注视前方,演员最后的结束形态,就是你的谢幕姿势,一切静止:用你的肩膀、你的脖子、你的指尖,即身体的全部,来充分享受掌声和欢呼,享受演出成功的荣耀。阿兰·巴士里要的是阳光神情,中国杂技教练们讲授过瞬间的职业“微笑”,但就是没教过“怎么静止微笑5分钟”。
不止一个演员说,练这样的微笑,比练个新动作还要难。“你试试看,微笑5分钟,肌肉就会不听自己的指挥,就会僵硬,随后,自己的心会动摇”。这个自自然然的“一动不动”,如沐春风般的微笑,所有演员花了1个月才慢慢达到要求。
对于52岁的副团长蔡荣华来说,掌声和欢呼,他早已听得太多。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时读过中国杂技史,了解到杂技原是有“身价”的艺术。“杂技、魔术、驯兽,在古代统称角抵、百戏。唐前,百戏不出宫廷,是专门为天子演出的艺术。宋朝之后,市民阶层兴起,百戏流入民间,在勾栏瓦肆设摊卖艺,一切礼仪就演变得简易、简陋,甚至‘残缺’起来”。巴黎人对谢幕的要求,让蔡荣华感到自己这个杂技人一夜之间的社会地位,回归到了盛唐年代。

25岁的徐滨滨,是从中国杂技之乡吴桥学校引进的尖子。一开始,他也不会笑。随着在巴黎两个多月的演出,他渐渐找到了感觉。作为一个杂技演员,打小走南闯北的他,终于感到自己在巴黎是一位艺术家。“法国观众热情,谢幕三次还不走,站在原地鼓掌,对我们欢呼”,“听翻译说,法国人看马戏和看歌剧的消费差不多,都算是高雅艺术”。
更意想不到的是,一台吸引人的演出未必依靠“讲故事”,也就是没必要详尽交待来龙去脉。新编《十二生肖》不设置完整的故事,只有一个基本情节,就是玉皇大帝依次召见十二个生肖动物。然而,舞台没有出现玉皇大帝,上来的只是卡通造型的生肖动物。事后证明,观众没有“看不懂”。凤凰马戏的制片方通过音效、灯光、人物服饰,把大棚气氛烘托得极其绚丽,人们像是被施受了魔法,运送到一个神幻世界,一切未知,一切正在发生,大家开始“如痴如醉”的一起做梦。
当然,绝活还是要的。每种动物都采用高难度动作出场。丛林中斑斓老虎的腾跃嬉戏,实际是金奖节目“大跳板”的360°旋、直体二周等高难动作的展示。一群小白兔的跃动,其实是“女子车技”翻版。在一面大鼓上矫健翻滚的白龙,也就是在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夺得“金小丑奖”的“男子单人造型”。蛇仙出场采用“绸吊”,羚羊盘角实际是“软钢丝”表演。胖猪和瘦鼠的滑稽转盘,在国内演出的具象是炊事班里的游戏。
赵雪说:“法国人提出修改的地方似乎都不大,但都很准确。这让我意识到,一个杂技节目的吸引力不在于制作方认为它是什么样子,而在于观众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法方的制作节目理念。”俞亦纲的概括是:国内杂技演出还是把难放在第一位,美和趣在其次,总想震住别人,而不是感染观众;最高级的故事“表演”,不必拘泥交代,重要的是要激发全体观众的经验感知和想象,来共同参与和完成“演出”,这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艺术能力。
从容自信的上海风度
阿兰·巴士里确实有赌一把的意思。
凤凰马戏的演出票不便宜,成人票70欧元一张,儿童票能打折,但也要15到20欧元一张。2013年的欧洲经济情况不佳,法国许多家庭已经取消了这笔开支。自当年11月始,至2014年初的演出,能否打响,赢得票房,是压在他心头一块石头。他希望:上海杂技团演出成功,媒体蜂拥,口碑诱人,“人们掏皮夹子的动作会爽快一点”。

登台的日子终于到来。在上海验收会议的两个月后,巴黎的凤凰大棚里已是一片“红色海洋”。入口帷幔是红的,脚下地毯是红的,环形墙壁是红的,5000个座席是红的,头顶的穹窿也是红的。场内红色灯柱交织映照,整个帐篷沉浸在一片梦幻而又煽动的氛围中。活动着的领位员服装也是红的。
观众就座,大多是家长带着两三个孩子的家庭组合。孩子们在翻看演出图册:12种动物围成圆圈,中间被一道“S”形曲线分为两半,两边各有一个点。孩子们的关注点,不是这个中国式神秘的太极造型,他们看到的是两条鱼。也有孩子在问父母,“我是哪种动物”?
中场休息。背着红色小箱的“小贩”们迅速进入场内,拉起箱盖,开始售卖冰激凌。孩子们忙不迭摇起了旁边大人的胳膊,这是西方剧场中最常见的一幕。不少孩子随着父母来到中庭的一块展板前,一个女孩尖声笑道:“我就想属狗,因为我喜欢狗!”一个男孩小声问“刚刚属了蛇”的母亲:“妈妈,你难道不害怕蛇吗?”
作为演出商阿兰·巴士里,通过打造中法文化通感,从而抵达业界利润,此时的他,已经在感受自己的成功了。
上海杂技人也在感受自己的成功。巴黎十二区,首演成功后的每个早晨,身穿红色工作背心的副团长蔡荣华就会走在这条明净的Minimes大街上。经过地铁站,再往前一点儿,有一家烘培房。蔡荣华向柜台里的金辫子姑娘竖起两根手指:“twenty ,bread, this”(20个面包)。姑娘拿出两根法棍。蔡荣华摆摆手:“No, twenty, two-ten, twenty.”(不对,是20根,两个10根,20根)姑娘终于相信她要一口气卖出这么多。排在后面的顾客耐心等待。一位法国老人瞅着中国人红色夹克衫外套背面印着的“phoenix circle”(凤凰马戏)字样,往外蹦出几个英文单词:“You, great, phoenix circle, very good”(“你们,很棒,凤凰马戏非常好”)。

演出迷住了大小观众 作者 供图
捧着两纸袋金黄的法棍,蔡荣华原路返回,走过白色木栅栏,就是凤凰马戏流动帐篷剧场的后台。后台是与帐篷无缝对接的一组板房,窗外的森林里鸟声啁啾。在上海杂技团的厨房里,井然有序地码放着装有土豆、鸡蛋、番茄和青葱的纸箱。国外的葱价格约是国内10倍,所以在当地第一次买回的葱都作了种子,在门外用大盆培土种植,“自产自销”。铁架上是酱油、醋、糟卤和大米,长条桌面上摆着煤气灶和半旧的电饭煲,还有洗净的不锈钢饭盆。
在厨房里忙活的壮汉,是大跳板节目的教练沈为民,凡出远门便兼任伙头军,身兼二职,为的是减少一个人工的成本支出。演员们每人一碗热腾腾的中式番茄蛋花汤,搭配咬劲十足的法棍,便经常是演员们在候场时候的点心。
2014年1月12日,上海杂技团的《十二生肖》在凤凰帐篷剧场演出最后一场。阿兰·巴士里手握上海杂技团的演出成绩单:从2013年11月14日首演至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十二生肖》上演76场,观众人数超过35万人次。在整个巴黎大区16个马戏团的打擂战中,选择来观看《十二生肖》的观众人数是最多的,这也标志着在与“太阳”的竞争中,上海完胜。当然,跟在票房数字后面,还有一个属于商业机密的盈利数字。这大大超过了法国人的预料,一霎时他还有点不相信。
他必须表达自己的谢意。中场休息时间,赵雪得到法方剧务传来的消息,她来到后台告诉大家:“待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阿兰·巴士里邀请中方所有教练、工作人员和领导,全体上台。”
谢幕时刻,团长俞亦纲、副团长蔡荣华、教练兼大厨沈为民,还有陈姝苗、赵雪、徐滨滨等40多位上海杂技人,挺立在舞台前沿,享受掌声,享受欢呼。阿兰·巴士里手执话筒致辞。法国观众们看到的,是一位同胞、一位演出商无比兴奋的脸庞。对艺术,法国眼光是高雅的,也是苛刻的;应对这份高雅和苛刻,上海杂技人的现场风度是从容和自信。舞台上没有翻译,但所有人都知道,阿兰·巴士里是在说,这是一台原汁原味的中国杂技晚会,自己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上海杂技团,来巴黎做这样精彩的演出,希望将来能够继续这样良好的合作。
向永恒的中国之美致敬
在巴黎凤凰马戏大棚的演出大获成功。对上海杂技团而言,可谓是实现了自己完美的涅槃。然而,事情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只是刚刚开始。
巴黎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法同行共同定制的那件“华丽外衣”,凤凰马戏的核心竞争力是它的整体创意、包装和合成。与“凤凰”共舞,对上海杂技团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学习机会,在近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在“实战”中琢磨和消化法方的行业规范和制度,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以及自己如何掌握话语权的能力。
感悟的,还有差距。凤凰马戏市场部在每场演出后,都会认真地进行问卷调查,请部分观众填写观后感受,综合后将结果、分析和“整改”意见上报给阿兰·巴士里。演出的“蹬板凳”节目,最后一段是令人屏息的巅峰炫技,但调查结果显示,不少观众看到这里觉得“时间太慢”。法方立即与中方商谈,哪怕取消难度最高的那几个经典动作,也必须把炫技时间缩短。
在演出后请观众填写字面观感,这是中国杂技业界从来没有想到和做过的事情。问卷调查的弦外之音,非常清晰:对诸种“惊险”的对人能力的极限挑战,外国观众并不喜欢,甚至反对。杂技是世界语言,表演有意境高下;内外有别,必须与时俱进。法国家长们最喜欢给孩子们看的,不是“最危险”,而是富有表演性的轻松诙谐的节目。
法国人对第三个出场的《舞空竹》,给予了最高评价。舞空竹是中国民间游戏,演员巴建国另辟蹊径地使用单轴空竹,使其舞动起来呈水平圆周飞行,“行云流水”、“望月”和“九节鞭盘颈”等技巧令人眼花缭乱。根据巴建国的形貌气质,编导将他“包装”成一名头戴斗笠、腰束长带、手执长鞭(空竹),身背竹篓的华夏游侠形象,轻盈飘逸。编导更在场上设置了一个“非杂技”角色:特邀一位“非杂技女演员”出演“琵琶女”。在中国民乐伴衬下,身着旗袍的典雅佳人轻掩慢捻,潇洒男儿灵动跳跃,两人心有灵犀,互诉爱意。这个《舞空竹》是上海杂技团编创得最有新意,也最不像“杂技”的一个节目。
在上海商谈演出细节时,阿兰·巴士里担心,“琵琶女”会抢主演的风头,“巴黎那么多观众没法明白这种安排的文化含义”。俞亦纲对他说:“你放心,绝对相对益彰”;剧团到巴黎,阿兰·巴士里还在“将信将疑”。
任何文化的第一特征就是地域性,“这个节目的技巧不是最高的,但它是一个散发着优雅气息的编排,具有中国特色”。在现场,浪漫的法国观众伸出双手,热烈地拥抱了侠男琴女的迷人场面。高傲的阿兰·巴士里低下头来: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景。
法国《费加罗报》的评论,则向上海杂技团的巴黎凤凰之行,高高举起了庆贺的酒杯:“向永恒的中国之美致敬”。

《十二生肖》演出现场 吴越 摄影

《十二生肖》之蛇魅 吴越 摄影

耳目一新的开场亮相 吴越 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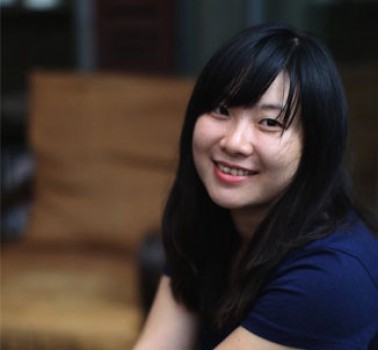 吴越,1983年生于上海。上海作协会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士,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大学毕业后进入文汇报工作,记者生涯十年间,曾任两届首席记者,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上海新闻奖等。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编辑。散文和纪实作品发表于《美文》《书屋》《笔会》《夜光杯》《上海纪实》等。
吴越,1983年生于上海。上海作协会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士,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大学毕业后进入文汇报工作,记者生涯十年间,曾任两届首席记者,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上海新闻奖等。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编辑。散文和纪实作品发表于《美文》《书屋》《笔会》《夜光杯》《上海纪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