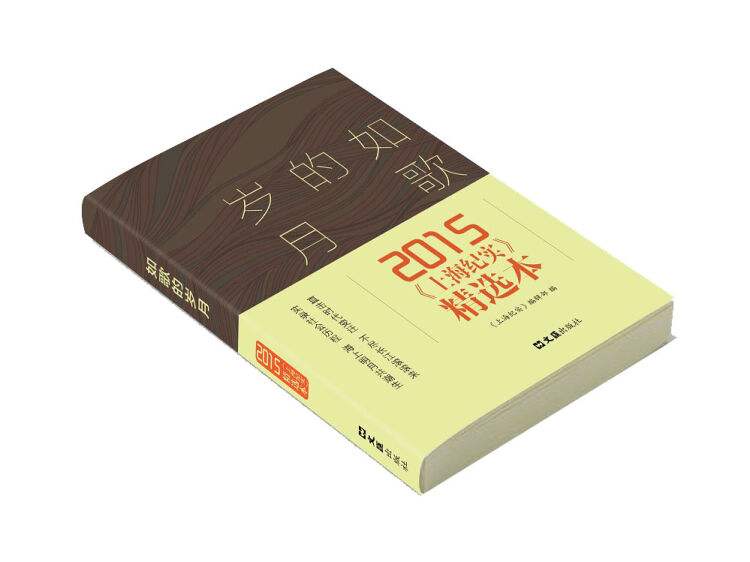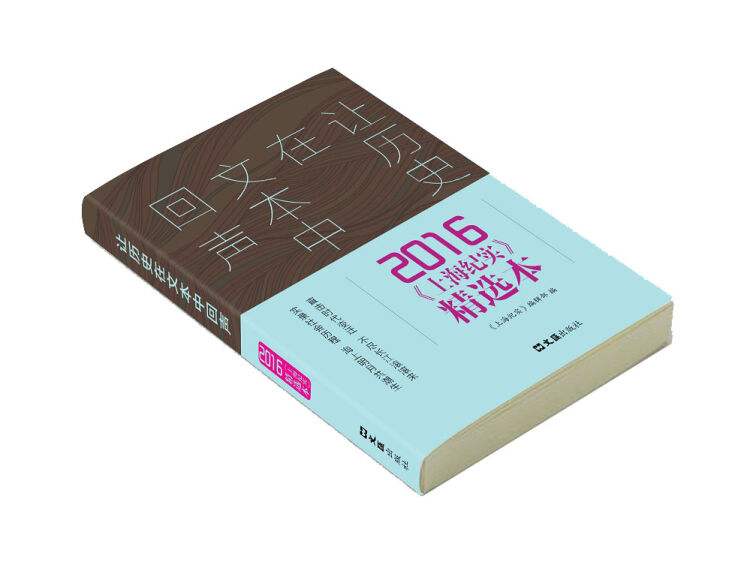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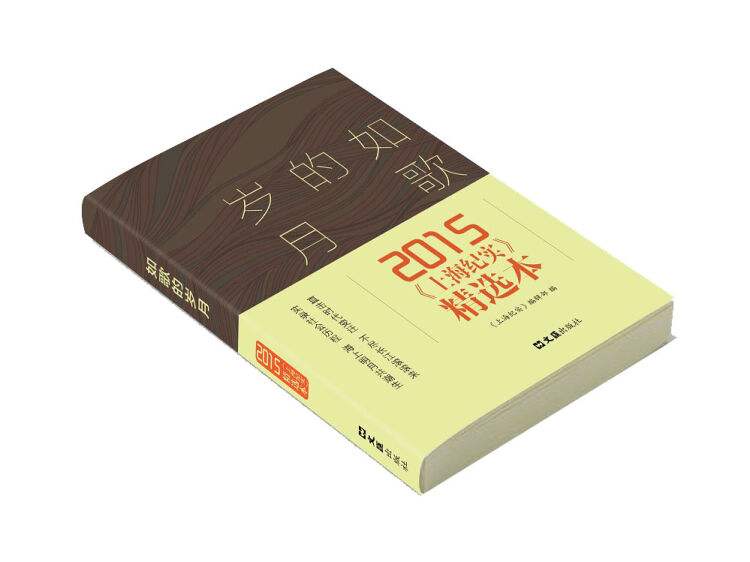
记录,访谈,日记,人物专访,纪实文体集中亮相于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这一特殊的时代现场,互联网的互动性和即时性更加倍放大了文本所承载的信息量和情感力度,事件,人物,情绪,思考……文字并不因为影像的繁荣而失却其力量,而在具有互联网特点的传播中获得多种面向的阅读和审美价值。
书桌上一直摞着四本厚厚的《上海纪实》2015年至2018年精选本,从《如歌的岁月》,而《让历史在文本中回声》到《拂去烟尘》和《生命的密码》,每本字数从50万到75万不等,从创刊于2015年5月的电子刊物《上海纪实》(季刊)中精选而来,凡“弄潮”“在场”“亲历”“记忆”“往事”“万象”和“风情”七大栏目,从栏目名称也能大致感知其间内容既追溯历史往事,又直击时代变迁,并描摹社会时代之宏大叙事,也表达具体而微的个体生命存在。每篇文本汇聚在一起,撞开时空的多维向度。
顺便一说,《上海纪实》(电子刊)在2020年春天抗疫防疫期间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推送了37篇上海作者采写的抗疫主题文章。或采写亲临一线的医护人员如何惊心动魄地参与救治病患,或描写自身参与社区抗疫防疫工作,或叙述上海各个行业在疫情期间的踏实感人事迹。这也因此成为在新闻媒体之外的有力的纪实文学表达。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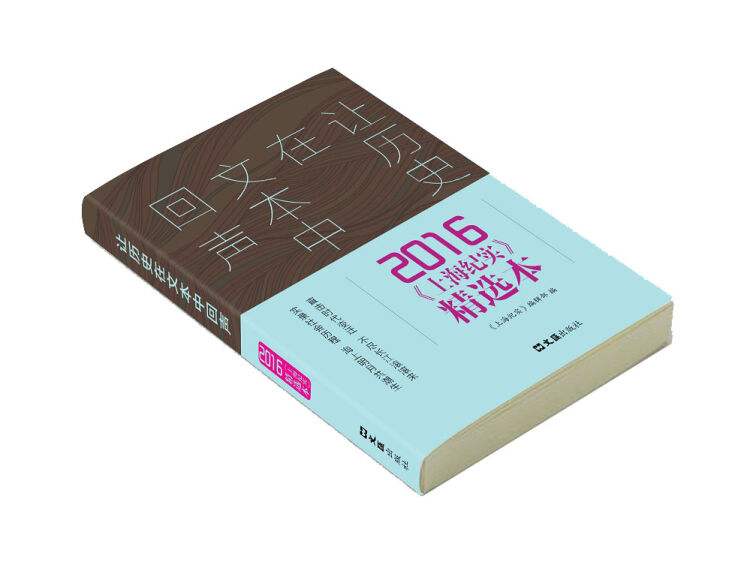
四卷的目录密密匝匝,那些角角落落、肌理筋膜的社会/个体内存在一字一字的排列组合中,成为丰富斑驳的块面,召唤起阅读者的视野,感知,共鸣,无论你在场不在场。作为个体,也许你忽然觉得你足下的半径扩展了许多,尽管你并未远足。
二三百万字的体量放在一起其实是让人一下子难以有明晰的逻辑的把握的,却分明让人心头一热,是文字给你带来了解外部世界的热切,是伴生着字里行间引起感鸣和思绪的情感。它们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从社会大事件到城市的细部皱褶。你看到《山高人为峰——“上海中心”建造纪实》(陆幸生,2015年)这样的沸腾的眼前的城市地标;你看到《与黄宗英争议小木屋》(罗达成,2015年)这样似乎久远其实不过30年前的热情执着;你看到《书斋外的学者——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彭小莲,2016年)中描写的如此刚正不阿的人品人生;你看到《生命的承诺与坚守——“大地母亲”易解放的植树造林之路》这样的人间的大爱和坚忍不拔(王萌萌,2016年);你看到《心之途,新之旅——记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杨绣丽,2016年)中一群在钢筋水泥的大都市中从事绿色健康社区事业的人们;你看到《画坛伉俪》(朱大建,2017年)的跌宕多姿的艺术人生;你看到《30年前采写邓公小平在中国开股市》(何建华,2018年)这样激荡的历史瞬间;你看到《如火的青春,如歌的岁月——记巴金的抗战岁月》(周立民,2015)这样历史和生命相互交融的往事;你能看到《上海工人新村的表情》(徐芳,2017年)之上海城市的肌理,以及如《寄声浮云往不还——且熟且陌五角场》(龚静,2018年)之现实和历史交错的人文地理;你也能看到《我的窠娘——上海弄堂里的最后一个“出窠娘”》(叶良骏,2018年)如此风俗和人生和风情为一体的人物形象,还有《一座城市的合唱——上海业余合唱现状描述》(孙小琪,2016年)之现代城市社会的文化生活一个侧面;你还能看到《崩盘》(天谛,2018年)中表面风光精彩却险象环生的投资实战……所举这些实在是四册《上海纪实》精选本之零星篇目。目之所及,所有的文字都扑面而来,所有文字裹挟的信息流能量满满,只让人感到它们所包涵的丰富和宽阔,一篇篇文章似乎不过一个个侧面,一旦集合成体,蔚然壮观,当下的热切涌动和历史深处的层岩跌宕,个体的生命感受和记忆,城市街巷的人和事的缠绕和彼此成全彼此的作用与反作用,所有的物理和抽象交汇成文字创造的时空。
这样的气象很自然令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盛况,同时也很自然地忆及1990年代报刊上所称为的“大特写”“长篇采访”,虽然我并不认为当时的报告文学样式或大特写和当下的纪实文体全然一致,但文脉上自有相承之处。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1980年代可谓风云激荡,思想撞击,社会文化经济焕然于以往,人心人情人事群情迸发,诗歌有“重放的鲜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小说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哥德巴赫猜想》、《小木屋》等一大批反映时代人物、社会关注的报告文学亦应运而生。其时上海文汇报主办的《文汇月刊》可谓一时之引领,每期必有亮点文章,每篇文章文前文后的故事在时任副主编罗达成先生退休后所著《八十年代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十年》一书中得以详尽和激情丰富的呈现还原。笔者当年亦自费订阅《文汇月刊》,一月一刊收到时急切阅读的情景犹然在目。今览此书更知一份好杂志背后主编编辑作者各自角色的倾情投入。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不同的文学体裁共同合力构建了一个或与现实相辅相成,或与历史回旋往复,但始终注力于人性人情人心社会历史的思考和拷问的文学世界。
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小说相较,在直击时代社会热点上的反应是比小说的沉潜往复迅速的,但也并不因此削弱人物的塑造,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笔下的陈景润,黄宗英《小木屋》中的徐凤翔都有血有肉,而作者贴近人物,甚至与人物同吃同住同甘苦(如黄宗英高龄入藏)的全身心投入,使这些报告文学甫一刊布,即一石激浪,昭显文学于人的心灵召唤。说来笔者后来去西藏的念头大概正是从读了《小木屋》开始的。报告文学乃新闻报道和文学性表达的结合,比新闻报道更深度挖掘以及文学化的叙事表达。在1980年代的背景下,报告文学和当代小说同为社会时代价值和审美担当可谓实至名归。到了1990年代,报刊媒体的发展使“大特写”这一类似报告文学的文章一时兴旺。市场经济,产业转向,下岗,下海等时代剧变使社会更为复杂,人性的展现也更为多向,“大特写”的记者深入一线的不少采访引人入胜,呈现社会多种向度。但不得不说,19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中有一些变异为一种变相的“软文”,企业出资,文字传扬,报道宣扬多之,文学审美少之,报告文学生渐渐衰微之象。然而,在21世纪的当下,也许是“非虚构”概念的引入,纪实类文本再度兴盛,或者,其实应该说纪实文体其实从未离开,不过,因影视、图像、游戏、动漫等多种文化娱乐方式的并存,文学包括纪实文本的被关注度缩小罢了,或者说真正的读者从未离开。也或许可以说,只要呼应读者心声的好作品始终会和读者彼此共生。
二

这里需要梳理一下“非虚构”这一概念。其实它源于国外高校中设置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专业,学制2-3年,主要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种。其中又细分为诗歌、小说、散文、传记、剧本创作等具体方向。学生以小说或散文或剧本等类型作品毕业后授予创意写作硕士学位(MFA in Creative Writing),MFA的英文全称为Master of Fine Arts(艺术硕士)。国外是将创意写作归入大美学学科,与其他工艺美术、电影制作等同属一个专业门类。笔者任职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于2009年国内高校首次设立MFA创意写作专硕学位点, 从2010年开始招生,至今近11年。主要设立小说和散文写作实践、散文经典细读、从小说到电影、创意写作高级讲坛及文艺创作方法论、西方文学名著选读、文学与宗教叙事等等课程,当然还有文学史课。课程设置的思路不仅围绕写作一项,是既在学生中创建写作实践和讨论的氛围,又有文学史的纵向思维,以及拓宽阅读和审美视野(深度)的宗旨。
笔者曾于2014年7月与同事们一起去墨尔本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学术交流,他们的课程设置分类比较细致,除了“Creative Non Fiction”(非虚构)、“Poetry”(诗歌)和“ Novels”(小说)这样比较常见的,还专有“Short Fiction”(短篇虚构)。在戏剧写作这样的大类别中,还分为“Script for Performance”(演出脚本)和“Writing for Theatre”(戏剧写作),在我理解中就好比一般的综合节目或通俗情景剧脚本和严肃的莎士比亚式的舞台剧之别,他们还细化到有“the Dialogic Imagination”(对话想象)和“Graphic Narratives”(图像叙事)这样的课程,当然这些课程是按研究生的不同学年设立的。我感兴趣的是这样的具体训练可能也有助于虚构或非虚构文本的局部推动的实践。个人以为,无论课程设置上的多少或差别,培养学生们的写作自觉和将所见所闻所思等素材转化为文学表达的旨意都是一致的。这大概也是创意写作的多元特色所在。也许也因此,国内不少高校的MFA专业,有的创办于戏剧学院,有的建制于中文系旗下。
非虚构文体相应于虚构(主要是小说,戏剧)而言,放在中国文学的谱系中,古代即文章,现当代大体指散文。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文体,其实就是增添了新闻性叙事性的长篇文章,只是可能与习惯审美中的篇幅不那么长、多抒情的散文而言,这样的文体需要一个命名,这也可以解释在1990年代一些评论者将余秋雨夏坚勇等一些作者的长篇散文称之为“大散文”,将一些短小的、从日常生活出发的文章称为小散文,好像一谈历史就“大”,一谈生活就“小”。个人是向不对此以为然的。文章有长短,但深度内涵境界并不完全因篇幅而必然“大小”。长篇宏制,短章精悍,并不对立矛盾的。
言及此,其实在所谓的“大散文”概念提出之前,当然更在如今之“非虚构”概念引入之前,1992年2月出版的杨绛《干校六记》(其实,该书最早于1981年5月香港出版)就是一部语言平实隽永,内容深邃却表述节制的非虚构佳作,薄薄三万多字的体量,一本小册子,至今读来依然回味无穷。作者克制冷静,细微处点到为止留白深远的文风和内容相得益彰,使人知晓彼时的历史情状,也使人透过那些克制冷静叙述,去探究更多留白处的幽邃。历史叙事、场景和情境的描述、通过对话刻画的人物、叙事者深刻体验却传达清幽的情感,在《干校六记》中如黄公望之富春山居图一般每一笔线条每一笔皴法每一笔点厾都值得回味。只是,1990年代将之称为散文作品,并未以当下的非虚构概念论之。时间流逝,好作品依然在时间中,如同礁石。好作品,并不需要什么概念来定位它。好作品,就是其本身。
非虚构的现实(历史)题材特征,于作者而言,既有个人经验的表达,亦多有对外部世界的探访,这样的写作于作者而言或建立起与社会与世界关系的更深更广的联结,于读者而言,亦是对现代社会中被同质化生活所困囿的一种突围。张望也罢,知晓也好,不一样的生活(历史)藉这样的文本而广角而长镜,带来不同视野和体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学领域向以“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这四大花旦分类,“非虚构”这一概念的近来风行,似乎让人感觉比文学分类中的散文文体更为外延扩展、内涵丰富的。其实在我个人的观念中,中国文学向有“文章学”传统,在古代文学系统中,凡韵文之外,皆视为散行文体,书信,论文,报告,甚至说明文,写人记事论学问,扎实的内容(细节)之外拥有作者的生命性情情致和思想内涵,皆为好文。窃以为非虚构文体大致如是。
散文,报告文学,非虚构,其实并不矛盾,只是文章的一体多面,侧重点不同的说法罢了。既为文章,自然因题材而取不同表达手法,表达侧重点也当相异。叙事视角的选择,顺叙倒叙插叙的结构安排,修饰辞采的随之而变,达意传情的分寸把握,意境境界的营造……既有印象派式的轻盈笔触,也有写实如维米尔式的细腻描画,当然也有泼墨风神的徐渭式的写意,而多元手法的运用,在一定体量的文本中就得以获得丰满的复调式的美学风格,比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等长篇非虚构作品,访谈、多种职业的人物自述、报道、电视片段,加上作者看似“无技巧”的裁剪结构,使读者在一个事件中获得多种质地的声音,也促使读者既有阅读共鸣,又带来间离感的思考。这样的阅读不囿于书中具体方圆人物,而扩之为人类命运。也所以,体量厚重的非虚构文本通常比单篇文章容量丰富,从宽度深度上拓展了文本表达的疆界。
当然,不同体量的文本拥有各自的审美价值,并不能以长短来划分价值标准。窃以为,内涵和文本体量上的契合,所谓当止则止,恰是为文的境界。
回到2015年5月创刊以来的《上海纪实》(电子刊),可谓既是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承传,又呼应了当下非虚构叙事的阅读期待。21世纪以来,我们身处的社会新事物层出不穷,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且因高科技的加持而于社会多方面甚至发生颠覆性的变化,高铁,电商,区块链,房地产,金融,国际间的流动,城乡联动,大城市扩张,生物基因工程,人体还是那个人体,当然人心已不知斑驳多少,社会的肌理若凡·高在世,大概也无法描画其变幻的星空,文学如何来把握表现传达当下的社会、人事?
文学如何在影视之外传达当下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价值,诗歌是也,小说是也,纪实文体亦是也。小说在人物塑造的深入,社会生活的幽邃和丰富性上较有优势,虚构也使创作者能更放得开手脚或从细微处看人生,或从宏阔的历史深处听回声。但非虚构文体直面现实中人和事复杂处境的“在场感”,经由文字/图片资料再现历史情境的“还原感”,触摸现实(历史)的“直接感”,时代的横截面兼之历史的纵深感,在在引起读者的共感共情共鸣,也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审美价值。当下的非虚构文本中,除了《上海纪实》专事刊登纪实文章的杂志外,有些文学杂志也专辟有“非虚构”栏目,一些自媒体公号也常刊布名为纪实故事的文章,近年来的出版中也有不少佳构。有的作家深入家乡,采访外出打工的人群,从家乡一地辐射当下时代社会,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有的作家返回家乡,描述以前忽略的父老乡亲,比如阎连科的《她们》;有的作家以陪护身患阿尔茨海默症亲人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坦诚记录病患和家属面对衰老、生死、爱痛等复杂情感,直面阿尔茨海默症这一既是疾病又是老龄化社会的特殊症候,予人(社会)沉思和关注,比如薛舒的《远去的人》;有的作者以亲身经历,写出在第一线的打工妹生活和心态,比如安子的《青春驿站》;也有写作者深入比如ICU这样的急救中心,采写生死一线牵之间的“人间世”。等等。
无论何种题材,纪实文体的“纪实”两字是最基本的底线,可以适当情境想象,或者揣测描摹,但题材的真实性个人以为是必须的。不少论点在讨论非虚构作品时会谈到非虚构之虚构问题。比如美国作家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说过“散文家为什么必须生活在栅栏里,而且还是带电的栅栏里呢?”(见《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雪莉·艾利斯 编 刁克利 译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P51),他虽然幽默地反驳了读者对其《岁月如沙》一书中的事实问题,而且如JENNY BOULLY所云:“在散文写作中挣脱‘事实’的束缚”。但是个人以为非虚构文本基于事实依旧是所需遵循的基本。当然有的文本采用采用虚构和非虚构模糊之叙事策略,或者自传体式的小说,但这些在我看来是创作者有意在文体上的尝试和突破,同样的,非虚构文本当然可如爱默生曾说过的那样,散文写作就应该像用泛琴演奏交响乐一样,“允许出现任何内容——哲学,伦理,神学,批评,诗歌,幽默,娱乐,临摹,趣闻,笑话,口技——最自由的交谈,最高雅和最低俗的个人话题所表现出的生机与多样性,所有这些都是被允许的,都可以被运用到一篇演讲当中。”(见《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雪莉·艾利斯 编 刁克利 译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P52)多样性,多种写作手法,但“事实”和“真实”作为栅栏还是存在在那里,好比你叙述一个梦境,并落墨于纸,或许梦境和现实亦真亦幻,亦或许“盗梦空间”般消弥梦和现实之界限,但你的梦如果是你叙述的起点,你写下梦境,这是一种文本的事实,而非现实的事实。当然,以量子学角度而言,所有的现实和非现实都是一种量子纠缠,亦真亦幻,好比“如梦幻泡影”,但窃以为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表达了,属于大宇宙观的观照。
三

在《上海纪实》(2015-2018)一套四册的精选本中,充分可见纪实文本的多元表达。“民心民意给了我良知与勇气——回望四十年前话剧《于无声处》创作演出的”(宗福先,2018年)是亲历的历史回顾;“生命之种”(童孟侯,2018年)叙写已故植物学家钟扬教授的人生,但事实上作者写作时已不可能面对面采访钟扬,作者以钟扬留下来的事迹为主要素材,采访其身边的学生、朋友,但因了作者对写作对象,热情深情,对植物学本身的兴趣,对生命种子的理解,依然写成了一篇具有深度和审美价值的文章。再比如说“一百年前的上海外语补习班”(沈嘉禄,2015年)是基于史料的钩沉和打捞,但也并不影响作者在文章末尾以想象性的叙事语境传达久远于时空深处的补习班的画面。而“韬奋先生在上海”(孔明珠,2015年)以采访韬奋女儿邹嘉骊女士为切入点,但正文以第三人称叙述,直接传达邹韬奋先生的生平事迹,将采访对象的讲述和史料细节融汇起来,而女儿邹嘉骊的回忆,又将历史的场景成为生动细节推至读者眼前,作者和访谈对象,和访谈对象中的爸爸邹韬奋,三个叙事点,在尾声部分有机结合于一体,这样的叙事在于篇幅较长的人物题材纪实文本中好比电影的推拉,近景中景远景,可以多角度多方位演绎。比如“画坛伉俪”(朱大建,2017年)叙写乐震文和张驰这一对画坛夫妇,作者的笔触深入人物成长生长、发展的方方面面,吸收了小说叙事的笔法,还原人物学艺修艺修身的诸多场景细节,栩栩如生,让人身临其境;等等。类似文本在《上海纪实》这套精选本中比比皆是。这样的纪实文本经读耐看,所谓“虚实互藏”,疏密恰当,文辞依题材而约而博,始终贯通着写作者主体之气息,在事实的“栅栏”上攀援着馥郁多姿的审美的蔷薇。
以个人写作体悟来说,我在写长篇非虚构《西门,西门》时,设置了一个第三人称“静岚”的女孩视角,以之串连起嘉定西门及嘉定城中周边乡村等方圆,将江南古城和大城市之郊区两者共融为一体的嘉定作为观照客体,兼及少女置身于西门的人事风俗之变化中的成长,以及以当下对过往的观照等时空交叉的视角变化。第三人称视角的设置,一是使作者和文本,产生一种观照省视的间离效果;二是我也视第三人称的“静岚”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她在叙述的推动中和周遭人事发生关系,在叙述时间中获得生命的成长(第一章节也收入于《上海纪实》2016选本中)。这样的创作实践也是希望在纪实文本中融入多种表达手法,并不囿于单一线性单一结构。比如像《回望》(金宇澄 著)这样的回忆性文本中,作者加入历史文献、书信、资料等拼贴,丰富了文本的整体内蕴,看似统一的叙事调性时被打破,但文本内部反而获得增值,并且这些拼贴来自叙事者的选择,它们的被看见其实正是写作者精心的构制。
名之为散文,名之为非虚构,名之为纪实文学,或名之为报告文学,个人以为是纪实文体一体多面,我还是更愿意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文章”这一概念。面对不同题材,选择不同的表达手法。有偏向于叙事的,偏向于说理的,有偏向于诗意的,于创作者而言,有的比较零距离,对题材的打量比较客体化,有的则倾向于历史梳理,有的和所表达对象生命交汇紧密。怎么去写作,某种程度而言,也是作者对人和世界的一种思考观照的方式。不过,好的文本一定饱含创作者的“有情”“有思”的打量,于此,如何以文字来较完满地表现题材,完成一个有丰蕴的文本,这才是比概念的命名更为要紧的。而好的纪实文本值得在多年以后回望,不单一时之作,不仅时代横截面,而成为历史坐标中的一个节点。确乎合了2016年《上海纪实》精选本的书名——《让历史在文本中回声》。而书写,亦恰是“拂去烟尘”,浮现时间和生命的纹路。
注:《如歌的岁月——2015<上海纪实>精选本》《让历史在文本中回声——2016<上海纪实>精选本》 《上海纪实》编辑部 编 均为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版
《拂去烟尘——2017<上海纪实>精选本》《生命的密码——2018<上海纪实>精选本》 《上海纪实》编辑部 编 均为文汇出版社2019年9月版

 龚静,上海嘉定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出版有《西门,西门》、《花半》、《遇见》、《行色——龚静散文精选集》、《书·生》、《写意——龚静读画》(初版和修订版两种)、《上海细节》、《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要什么样的味道》、《文字的眼睛》及《城市野望》等二十多部散文随笔集。
获第三届“上海文化新人”荣誉称号(2000年)。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2006年)
。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2014年)。2014、2016和2019年度上海市作协会员年度作品奖励(散文集)以及其他文学奖项。
作品被收入《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散文卷》、《繁华与落寞》、《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你可以信赖他——‘2002笔会文粹》、《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2004笔会文粹》、《新时期嘉定作家群》(作品卷/资料卷)、《2018民生散文选》及《清澈的理性——科学人文读本》等多种散文选集。
散文作品曾被翻译成英文收入选本出版。诗歌作品入选《上海文学》英文版首刊。作品曾收入上海市高中语文课本。
龚静,上海嘉定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出版有《西门,西门》、《花半》、《遇见》、《行色——龚静散文精选集》、《书·生》、《写意——龚静读画》(初版和修订版两种)、《上海细节》、《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要什么样的味道》、《文字的眼睛》及《城市野望》等二十多部散文随笔集。
获第三届“上海文化新人”荣誉称号(2000年)。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2006年)
。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2014年)。2014、2016和2019年度上海市作协会员年度作品奖励(散文集)以及其他文学奖项。
作品被收入《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散文卷》、《繁华与落寞》、《上海作家散文百篇》、《你可以信赖他——‘2002笔会文粹》、《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2004笔会文粹》、《新时期嘉定作家群》(作品卷/资料卷)、《2018民生散文选》及《清澈的理性——科学人文读本》等多种散文选集。
散文作品曾被翻译成英文收入选本出版。诗歌作品入选《上海文学》英文版首刊。作品曾收入上海市高中语文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