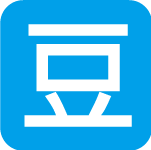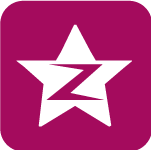一个老松江人的忆旧
钱明光朋友拜访我,想以老松江为背景拍一部电视剧,并先拍了些片花找找灵感,毕竟老松江故事很多:施蛰存摆了四鳃鲈鱼婚宴、程十发的婚房就是他出生的老宅,赵家壁离开松江那么多年还记得家乡的特产酱小茄、罗洪以母校为题材写了部长篇小说——但我看了片花后对他说你还没有足够了解旧时的松江。如,过去家家都有蛮大的灶头间,要放灶头、大水缸、稻柴,所以单间人家是没有的;过去姑娘都是束胸的,胸大会被人家叽叽喳喳议论,所以人物不能太性感。过去文盲多,街头代写书信的摊头不少,用钢笔是后期的事,过去都用毛笔。后来,我就干脆带他各处走走、介绍下旧时的松江。
一个独有的节日
松江过去有条三公街,位于方塔旁。三公是指哪三公?因为历史上把皇帝谥号文敏的元代客居松江的赵孟頫和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张照合称“松江三文敏”,好多人都认为指这三位。其实,这“三公”指的是明代的董其昌、明末的李待问、清代的沈荃。三公街上因有董其昌祠、沈荃祠和李待问庙而得名。沈荃是在皇宫为官的书法家,我国书法“馆阁体”的代表人物。李待问就是松江独有节日的主角。
年纪稍长的一些“老松江”还记得,1961年以前,松江城墙还在,每逢农历七月十四,长长中山路上,西门口两边、岳庙内外,街上尽摆铺板,摆满一碗碗豆浆,而旁边一只只热炉油锅中,忙碌地在氽着油条,夜幕将临,全城百姓携老扶幼,倾城而出,上街吃豆浆油条,景象蔚为壮观,此乃松江三天“鬼节”的开始。后两天,从西门吊桥口到云间第一楼,是热热闹闹的松江庙会。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庙会上购买首饰挂件、购买缸甏铲刀、品尝着糖芋艿、“扁担馄饨”、“老虎脚爪”。这就是长三角中松江独有的节日盛况。

旧时廊棚
这个节日始于何时?为何有此节日?
这个节日始于1645年,为纪念东门守将李待问的。
李待问,松江府华亭县人,家住榻水桥堍,1643年考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李待问写得一手好文章,亦有一手好书法,书法笔力遒劲,字体秀逸,行书可与董其昌媲美。1645年,清兵下江南。李待问与陈子龙、夏允彝等名士起义抗清。先是鲁之屿率三百勇士攻苏州,结果全军覆没。后又闻嘉兴失守,松江形势吃紧。主心骨夏允彝又投松塘而死。李待问将老母亲迁于乡下,自己主动提出负责松江东门守卫。八月初一清兵攻至城下,松江军民团结坚守三日。粮尽弹竭,李待问与百姓一起用豆浆劳军。初三,清兵用计谋袭取西门,城被攻破。李待问见大势已去,乃从东门下来。有人问他,您熟读《四书》,今日如何办?李待问说,为臣死忠,这是常事,我不会投降,我只不过想和家人作最后诀别。那人说,你能这样,我也学你,我先断头等你,后拔刀自刎。到家后,他对妻妾说,我不能逃走,我要对得起百姓,遂后引绳自缢。但气还未绝就被冲进家门的清兵俘获。劝降不屈。临死仍劝说清将不可残杀民众。

水桥头
松江民众怀念他,尊他为府城隍老爷,并塑像纪念。因他诞辰日为农历七月十四,遂将“鬼节”三天从七月十四日开始。“鬼节”第二天即七月半,家家户户还应祭祀祖先。
此节七十年代后逐渐淡薄,但时至当前,方塔公园仍每年七月十四向市民赠送豆浆。
松江人也蛮奇怪,三个节名称直接用数字为名,如,元宵节不叫元宵节,叫“正月半”;端午节不叫端午节,叫“当五”;这鬼节是文化人叫出来的,老百姓至今仍称为“七月十四”。
一条珍贵的弄堂
松江曾经是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老城十分繁华,有好多条满是掌故的弄街,但在老上海心中,袜子弄是印象最为深刻的。袜子弄,这个名称怪怪的,街内既没有袜厂又没有袜店,街型笔直又不像袜子,怎么叫袜子弄呢?其实,它与松江灿烂的历史文化有关,它与中国资本主义的最早萌芽有关,它是记录松江当年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繁荣景象的唯一遗存。

1990年被拆前的长桥老街
明代,松江衣被天下,“买不尽魏塘纱,织不尽松江布”,每天经上海港外运的布匹多达上万匹。松江城内处处可闻机杼声,松江布声名远扬。经济发达了,就会开发新品。那时一般劳动阶层夏天是不穿袜子的,能穿、需穿袜子的也穿的是毡袜,后来穿的人多了,人们就开始研究用松江名布尤墩布加工暑袜,这种袜子既薄又轻又美观,经口口相传,各地商贾都到松江采购。袜子弄是这种暑袜的集散地。明华亭人范濂所著《云间据目抄》上记载袜子弄“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在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中国通史记载苏州、松江出现了机工机户的中国最早资本主义的萌芽现象,“店中给筹取值”,就说出了店主与劳务工的雇佣关系。这短短的几个字,闪闪发光,道出了中国一个新阶层的出现。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城内炸成一片废墟,已经没有明代松江棉纺织业繁荣的其它遗存。但这街还在。这是多么可观的一条街呀。不少历史研究者就曾呼吁过,要好好保护袜子弄,至少应在街头立一块碑,介绍此街。现在去成都的人都要去看看宽窄巷子,说明规划开发好了,会成为一个地方的主要景点,袜子弄是一个漂亮的村姑,急需合适的装扮。
袜子弄浓树遮荫,大道与平行的通波塘大河相隔一二十米,中间只有几间居民房,另一边是废弃的厂房。顾绣的挖掘重振就是在这条街的工艺品厂内。这条被冷落的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再次因顾绣的挖掘、传承引起人们的关注。街中间通一条小弄,名邱家湾,那小弄也很出名,有一很有名的教堂叫耶稣圣心堂,教堂旁边曾经是华尔洋枪队的总部。袜子弄街的中间有一座小木桥通向河对岸,过去通波塘河远没有这么宽,河的对岸有一座寺庙叫禅定寺,1919年,大画家张正权因思念病逝的恋人不能自拔,在这里削发为僧100天,在这里取了法号名大千,从此人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都只知道他是从这里出发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他的名字叫张大千。这条街的两边蕴藏着那么多的故事。夏夜,微风吹拂,灯光婆娑,是恋人散步的极好去处,过去松江可供青年人荡马路的地方不多,袜子弄因居民少,环境幽静,是理想的场所。如今城内好多五六十岁的“晚秋”辈,当年都曾经手指头拉手指头地在这街上浪漫过。
袜子弄还承载着老松江人当年的好多情愫。你不要看这街只有500米,却是连接松江城内与农村的主要通道。袜子弄城内这头有一个长途汽车站点,那些为远赴外地送行告别的场面都发生在这里。而在北端,那些从卖花桥、龙树庵挑着重担想进城换个好价钱的农民在这里深吸口气,然后忐忑不安地从这里向城内进发。当年,我被送市里学习,寒冬腊月的,需要凌晨5点在这里乘上去市区的公交车,务必要在8点前赶到三门路校区,逢周一我们就这样一伙人4点前起床,步行赶到这里,个别的学员有亲人骑自行车送过来,大家都替他们感到幸福和温暖。这种环境虽艰苦,但锻炼了我们的身体、磨砺了我们的意志,我们因此也对袜子弄有着无法名状的眷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袜子弄也热闹过,那是因为松江招待所在这街上。招待所是松江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无论是外省宾客还是外国贵宾,都在这里吃住、交流;来松江开地区性会议了,也只能在这里集中。每年几次的三级干部会议,千把人来开会,几乎集中了全区的大小干部,吃、住、讨论,都在这里。我记得,那时农村进城开会的,公社干部是用粮票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是带米领饭票的,开会报到时,最忙的不是签到处,而是门口的称米处。哪位干部说我不用交米有粮票,周边的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有的公社参加会的人多,就干脆自己开个柴油船直接开袜子弄旁河边停靠。所以,每逢大会,无论白天晚上无论路上街边河中,都很热闹。
如今的袜子弄,不知怎么的,好像是历史上最冷落的时期了,作为一个老松江人,偶尔路过,总有点歉意在心头。
一条江南难见到的大街
江南水乡,湖网交叉,无论城市或小镇,道路多逶迤曲折,但唯独松江有条十里长街,笔笔直,放在过去也应是宽宽的,从东到西有五点多公里,松江人称为十里长街,辛亥革命后叫中山路,明清时中段叫郡治大街,东段叫东外街,西段叫西门外大街。
那为何笔笔直呢?因为过去的交通都是水路,说那儿交通便捷是指那儿水道宽敞、水况良好。松江城既是府衙所在地,又是华亭、娄县县衙所在地。南来北往的商船,都要经过松江水上的交通枢纽;官船路过,或留宿,或休息,按规矩都要当地相应官员迎送。由于两地路远,接到官报,马上出发到目的地有段时间,就选择笔直的捷径了。从衙门到水上交通枢纽一条笔直的马道轿道,时间长了,就成了通衢大道。所以,这条大道的最西端就是接官亭、祭江亭。松江自明代起,人口因经济发达而急剧膨胀,“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城墙内已容不下过多的人口,城墙南北两门是水门,于是,大量人口就沿这条大道向两边发展,特别是向西部发展。松江在明代是进士高产期,外官回乡建屋和私家园林,都选在这道的两边,慢慢地,这路就变成繁华的商业大街了。至于松江的好多豪宅名园为何建在大道的东西两头?有两个原因:一是私家园林占地多,地价是个重要的选择因素;二是城内主要为行政办公地,从县府路、东司弄、西司弄、察院弄等名称就可以想象得到。
松江四鳃鲈鱼名扬天下,位列中国四大名鱼之首。传说只出在这条长街的秀野桥下。其实,这是个误传。四鳃鲈鱼喜欢咸淡相拥、水域宽阔、饵料丰足、江水朝夕有序的环境。其实在东北、苏北等好多地方都有发现。历史上文人骚客从三国时期到清代,吟诗作画,都把四鳃鲈鱼只与松江府地联系在一起,清朝一权贵曾经题联曰:“鲈鱼一尾四鳃,独出松江一府;螃蟹二螯八足,横行天下九州。”松江河多水好,本来四鳃鲈鱼产量就高,松江秀野桥下成了各地来采购的主要场所,“不辞轻舟来往疾,筠篮验取四鳃鲈”,说的就是买卖四鳃鲈鱼的盛况。秀野桥下是鱼市而不是唯一产地。
好多人说,在松江十里中山路上,可以“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此话不假。通波桥以东三四百米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经幢和宋代方塔;有我国最古老、保存得最完整的明代砖刻照壁;松江二中的门头是元代府城谯楼遗址,后人都以“云间第一楼”相称;中山路的中段,有宋代西林塔、元代清真寺、明代西林禅寺,有始建于公元1782年的老字号、上海最早的药店——余天成堂。中山路的西端,主要是以仓城为主的明清建筑群。今日仍可依稀看到“门前连市井,屋后闻橹声”的场景。
特有的炒烧饭与菜卤蛋
天渐热了,我又忆起三五成群左躺右坐、手摇蒲扇“嘎山湖”乘风凉的情景,那一道令人难舍又即将逝去的风景。
有朋友回松省亲,临别时他感慨道,人在外,常想起夏天,劳累回家,吃上一碗淘茶炒烧饭,加上两只喷香菜卤蛋,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啊,这种感觉是五星级高价餐饮所无法感受到的。我对他说,你的这种情结与施蜇存《云间语小录》里写得一样。
炒烧饭,是松江人特有的习惯。松江人把刚从大镬子里烧熟的饭全部盛在饭篮里,洗刷好镬子后,再把饭倒入其中炒至焦香味,再盛入饭篮里,挂在屋檐下通风处。炒烧饭的最大特点是耐饿。过去家家有菜卤,卤汁菜卤蛋,碧绿嫩黄,好看又清香。过去松江人有自己种田种菜纺纱织布绱鞋缝被晒酱腌鲜的习惯,自给自足能力特强,除盐外,终年身无分文日子也能过得下去,何况松江还是官盐的主产区。

过去的走街叫卖现在已习惯进星级菜场
明朝时,松江是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是全国三十三个工商城市之一。那时候,城里河道曲曲弯弯,许多房子临街枕河,舟船进进出出,多的是装运松江布匹的。城里男的织布浆布,女的纺纱并线,劳力不足,还去租男劳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苏州、松江一带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机工机户”现象。这些到城里打工的长工,已用上了当时先进的立式织布机,织出的布门幅稍宽。但站着干手工体力活很累,人家又不管你饭或点心。把饭炒焦了,可以吃得更多,更不易饿。何况,炒烧饭炒焦了不容易馊。菜卤蛋又香又便于携带,饭篮里一放就可以了。渐渐地,炒烧饭、菜卤蛋成了松江人特有的饮食爱好和习惯。
松江的经济繁荣催生了松江画派、松江书派和松江顾绣的形成,也促成了松江成为中国“苏松税赋甲天下”的两大区域之一,松江也成了全国进士出得最多的地区之一。多年以来,松江人一直沉浸在这种繁荣的记忆中。及至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出现了大量现代化 的纺织厂,“洋布”、“洋油”、“洋火”大量从上海通过长江运往全中国,有衣被天下之誉的松江急剧衰落。上海从一个小县城跃升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松江从工商城市退回到农业大县。大量苏北纺织女工的涌入,也使上海各纺织厂、织布厂门口开起了许多小摊点,原盛于苏北的茶叶蛋从此涌入了上海。
松江上了年纪的人至今都不爱吃茶叶蛋,甚至骂人都把“去你妈的”骂成是“滚你妈的五香茶叶蛋”,这种骂人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常能听到。特别盛夏之夜乘风凉吃夜饭时,依稀能听到:
剥一只菜卤蛋,
盛一碗炒烧饭,
酱瓜脆,落苏咸,
滚你妈个五香茶叶蛋。
一个特别的生产队
现在松江城南的乐都路,过去是松江最北面的一条军工运输公路。我当知青就插队落户在这条路边的农村。
我这个生产队有点与众不同。傍着通波塘河边的队,与其它地方并不两样,但,一座很大的天主教堂怎么会选址于此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试验新的鞋码,就是把如39、40码这种只讲长度的编法想改成如24-1型、25-1型长度加宽度的编法,据说全国选五个点,我们生产队被选中了,每人量了脚的多项数据后发了一双解放球鞋;土改时,地委文工团蹲点也选上了我队,在我这个生产队还创作出了一首上海方言歌曲《啥人养活仔啥人》,在苏南盛传,一直到我读中学时,音乐课还在教。文革时,硬逼文艺团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海越剧团、上海甬剧团一批演员就在我队和邻队劳动。
我们这个生产队还有几样与众不同的,一是离城近,潮小船不能进小河时,人家等几天,我们会直接从城里挑步担把大粪挑回来,二是城里过去夜晚马路上像森林一样壮观的卖芦粟的队伍,多半是我们生产队的,三是我队河、浜、桥多,盛产荠菜。

明代大仓桥
不要说城里人,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也大多不知道什么是挑步担。挑步担是指城镇边缘的农村,在枯水季节,无法船运,农村又急需肥料,或者此时其它大队无法装运而清管所特批给城边生产队的计划外“临时粪”,需要人直接从城里的厕所挑到生产队的储粪池。
挑步担是很吃力的。看看是城郊,到城里闲逛是很近的,但要挑着重担走,就显得够远了。挑步担有两种方法,一种一步到位,大家一人一担一起走,中间打头的说休息,大家就休息,打头的再一声吆喝,就再一起走,不能有掉队的; 另一种是接龙式,每人挑一段,扁担不换换粪桶,这种方法我最反感,因为各家的粪桶绳长短不一,让我这矮个很吃力。
我在生产队横竖都是挑。大忙了挑秧,秧插好了挑稻,三夏三抢三秋忙好了,开始轮着有省力生活做做了,我却要到蔬菜田里挑水浇水,到城里挑粪上船。挑,我是不怕的。那时,与我搭档的老农凌晨二三点钟去“也是园”茶室吃早茶,我天亮后自己一个人摇着船到达某厕所,当时我对通波塘到西林塔,所有厕所哪一天满了,了如指掌。当时没有通信工具,但二人没有寻不到的。可我对挑步担很怕。
那年年初三,队长要我挑步担。因为挑步担是不能叫老农去的,于是派了6个青壮年,因我熟悉清管所的流程,所以队长把粪票给了我,又因为我与吊粪的那“右派”关系处得不错,每担粪吊得不容易吃亏,队长也理所当然叫我去。我们的行程是从竹竿汇中段的供电所厕所出发,经过窄窄长长的竹竿汇石板路,穿过中山路大街,进入黑鱼弄的弹硌路面,挑过很高的凤凰山桥,进入菜花泾的泥路,在菜花泾路的中段抄小路往北,挑过乐都路,进入农益八队,在这个生产队里继续往北,不到二里泾时再转向东,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
那天清管所柜台前又象往常一样挤满了人,在等待着调配“临时粪”,我径自上前,自傲地说出三个字“计划粪”,拥挤的队伍马上自动让开一条道,有人悄悄地嘀咕,他们怎么有“计划粪”的,我听见了,神气地回答,我们要为军工单位生产“战备粪”。
挑担,特别是挑长路,扁担的好坏是很重要的。扁担要宽,肩膀就不容易痛,又要软硬适中,挑时就有荡势,这样不容易累。挑长路又要有节奏地哼,这样呼吸就会匀称。但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那天我在竹竿汇石板路上挑就两次”急刹车”。两个小孩嘻闹着从小弄堂里冲出来,就在我面前,我若反应慢,他们就会撞上粪桶,新衣新裤就会溅上粪滴;一辆自行车超过我与我前面的大娘撞了,跌倒在面前。我要是刹不住脚步,也会与他们一起摔倒。过中山路很有趣,我的哼哼声,惊得节日穿着新衣的男男女女闻声而避。凤凰山桥又短又高,一步一步往上挑确实很难,弄不好前面的粪桶常会与桥面相碰。挑这几级台级总会让人内衣湿透,我就常在心里默默地背诵着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台词“最后的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来鼓励自己。
挑步担也有轻松的时候,那就是空担回程。挑着空粪桶一路看着风景一路慢悠悠地走。当然,一个更难更重更累的行程也在等着自己。
我插队时的生产队,社员们种芦粟门槛很精,芦粟总是又粗又长,而且糖分足,别的地方来讨点种籽回去,种出来的仍不及我们的甜。松江街头的卖芦粟者,多半是我队的。卖芦粟像赶庙会,煞是好看。
种芦粟时,家家户户,屋前宅后,寸土不让;自留地上也精心套种,高爽点的自留地更是连片作业。下籽前,无论是吃茶吸烟的男人,还是晒酱扎鞋底的女人,互相牵扯的话题,总是芦粟籽有没有被老鼠吃掉、一分地用籽多少、何时下籽日脚最好等等。种下后浇清水粪这段日子,男女老少都上阵。从黄昏一直忙到天黑碌碌,一边是家家灶头间飘来叮铃当啷的响声,一边是户外黑暗中不时传来粪桶粪勺的碰击声。别地方从未见这样认真过。
芦粟长大了,也正是三抢大忙阶段。每天插秧或耘稻,总要做到太阳挂在西边树梢,许多妇女洗尽一脚泥上岸回家,换上干净衣裳,着上清爽布鞋,掮上一捆芦粟上松江。大忙是不准请假的,唯有卖芦粟除外。肩扛芦粟从田中穿过,田中人会打趣:“铜钿银子又要来了。”那卖芦粟妇女会夸张地做出吃力相,一边自嘲:“生铁补镬子,我伲苦恼子。”其实是很开心的。
松江城里卖芦粟最大的市口在中山路上岳庙口和谷阳路口。每到傍晚,两边成排成排的芦粟笔挺竖在路上,每捆后面站着一位主人,倘若时间还早,也有互相打情骂俏的:“对面这个小后生,年纪么差不多,有了铜钿讨去我,呒没铜钿只好望望我。”“姑娘姑娘十八变,刚刚还在稻田里,三清四落上街去,回来只好叫我做女婿。”及至路灯亮齐,大街上乘风凉的人多了,这两个市口也开始人轧人了,买卖开始进入高潮。卖芦粟的都有一门小手艺,不用刀,可用两手一节一节掰下来,不会断在肉里,也不会拖壳带皮。若嫌芦粟太长不便当,卖主可利落地帮着一节节断好。折下的梢不要,卖主便拿回去做芦粟扫帚。

如今收割劳动强度大降
我们这个“芦粟队”,还有几样规矩。平日里做生活,做到那儿就在附近地里拔芦粟吃,无人计较,若已扎成了捆,断无人会去抽一根。还有,芦粟浑身没有多余的,叶子青时垫猪棚,干了当柴烧,梢梢头做芦粟扫帚。天气入秋,老人将做好的扫帚拎上一捆,扔在茶馆门口,自己去孵茶馆,有买者,自会寻进去。如要有人不小心把手割破了,出点血,不用红药水,把芦粟皮外的白霜刮下来往伤口上一抹。大家都信这招。

今日松江一景
如今,这里已被荣乐路、通波新村占据了,我常常望着这片楼宇林立的田地,高兴中总有点惋惜。
松江城北一里远,有条小河叫一里泾,位于我生产队中。窄窄的,斫草小囡草篮都可扔过岸;浅浅的,潮汛小时船都撑不进;长长的,有二三里,东边通着潮水蛮急的通波塘,西边有好几个池塘靠它透气。池塘一多田地就不正气,一里泾两岸畦地、自留地就多。一里泾灵气十足,传说颇多,但一里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岸鲜嫩的荠菜,有道是“菜花泾里桂花香,一里泾边荠菜多”。
节气真灵,立春一过,再冷的风都没有刺骨的感觉。万物还没有复苏,赤膊的泥地上开始冒出些许贴地生长的小草。这时候、河滩边、桥墩旁、池塘岸和田垄中,会冒出许多荠菜来。若天气再过个把月,万物扮春,荠菜就会淹没在万绿丛中,既难寻,又见老。
正月半,别的地方叫元宵节,只吃元宵;松江一带“正月半”就是节日的名称了,也不兴吃元宵,而是吃荠菜圆团或荠菜塌饼,真如清朝诗人所云:“闲从人日说平安,荠菜新鲜做粉团。”那粉团也就是塌饼。我们今天还知道荠菜有美食、营养、保健、药用等多种价值,荠菜味道之鲜美也尽人皆知,而老人们说,吃荠菜圆团或荠菜粉团主要是能刮去春节暴食留在体内的猪毛。因此,正月半必吃,而此时荠菜正好应运而生。
荠菜好吃识别难。正月初十一过,到处可看到挑荠菜的妇女、姑娘和小囡。斫草的小姑娘草篮里放只布袋,她们是见草斫草、见荠菜挑荠菜;大姑娘们手提元宝篮和小刀,她们是专负着正月半的使命的。荠菜有的褐色,叶子像百脚虫;有的碧绿,叶边没多少曲折;又与同时冒出地面的铜钿草和毛边草极为相似。有的小姑娘回到家,被大人将草篮或元宝篮扔在门外或一里泾河里,可听见他们的训斥声:这样笨还能嫁得出去,哪是荠菜哪是草都分不清,靠侬还吃得成圆团塌饼?往往又是奶奶在姑娘的哭声中细细开导:
“荠菜遍地有,
挑一漏了九,
不要到处寻,
只要往下蹲。”
还会再示范:“你看,上次已对侬讲过了,这叶背有绒毛的是毛边草,这叶子像孔雀羽毛的叫铜钿草。”大概识荠菜、挑荠菜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当糯米磨成粉、荠菜切成细末包圆团时,就有点过节的味道了。媳妇包馅,男人挑水,老人烧火,小囡里里外外蹿奔,同年夜脚蒸糕差不多,很闹猛。若心情很好,老人还会念叨起顺口溜:
当家男人出远门,
穷家富路备碎银;
老人小囡饿伤心,
活不下去荠菜寻;
金榜题名回家门,
问对荠菜亲不亲。
也可从杜甫“墙阴老青荠”度日的艰辛中知道荠菜的这一功能。
乃至后来,城里人也到乡下来挑荠菜,发觉一里泾两岸荠菜又嫩又多,出脚又只有里把路,挑的人就多起来了。乡里人一看,留不住这片风情了,也开始挑了到城里卖。从此,后辈也就难有“春在溪头荠菜花”的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