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岁月荒诞事
管新生令我印象最深的,是F君的“上海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因为有当时轻工业局第一把手马振龙的批示而闻名于世:这是发生在上海铝材厂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我,不但全程参与了,而且深深陷了进去。

管新生照片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严格地说,那个晚上已经不是晚上了,而是凌晨一点多钟到两点钟之间。
那个凌晨有点冷。我记得自己当时是披了一件比今天游荡在城市里的叫花子起码低了几个级别的上上下下全都争先恐后往外冒着白花花棉絮的工作棉袄走进防空洞中去的。
和平年代的防空洞并不防空,而是工人们休息的好去处。
我进了防空洞的时候,只见依墙而置的长条凳上已放倒了两条汉子:F君和“老江湖”。我刚在长凳上坐下来,对面长条凳上的棉袄一动,旋即露出了“老江湖”的大脑袋:“热轧车什么时候能修好?”
热轧车是在吃半夜饭前轧最后一方铝块时“轰咚”一声罢工的。我一边脱下棉袄一边回答:“机修组的人刚来,听说是轧辊断了,得换辊筒,大概要换到天亮吧。”
当我躺下身去并将棉袄蒙住脑袋时,听到了“老江湖”类似欢呼状的一声长吁:“看来,我们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接着便响起了F君的嗓门:“谁发出这么难听的声音,是杀狗杀鸡杀驴还是杀猴子啊?瞎叫唤什么哪!你不说,人家就不知道了?快睡觉快睡觉!”
“啪”地一声,F君随手拉熄了高悬在头顶的那盏灯。
F君从小就是搞体操的出身,头朝下脚朝上的拿大顶,凌空腾跃三五十个空心跟斗,或者来个七百二十度的“旋”,统统是小菜一碟,一碟小菜。他很受班组里男女老少的欢迎,一是肯干能干,有一把子总也使不完的力气,无论谁叫唤他一声,他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帮忙;二呢嘴甜,“阿姐”“阿哥”的老挂在嘴边,即使有时候做得过分了,只要“阿姐”“阿哥”的一气乱叫唤,谁还能狠下心来较真?更何况,一个班组里的人嘛,总有几个疯疯癫癫的喜爱胡乱开玩笑的,再大的事嘻嘻哈哈一笑,只要牵不上线挂不上纲沾不上“阶级斗争”的边,也就过去了。这样的结果,便造成了他有事没事的总喜欢惹惹别人,而所有的人也喜欢有事没事的总爱惹惹他,尔后彼此一笑,没事了,天大的事也就没事了。
“老江湖”呢,据说没进厂以前确确实实是个跑江湖的,无论到哪个码头,只要见着人多的地方,他立马在路边铺下一块三五尺见方的脏兮兮的白布,立马扯开他打雷一般的嗓门,不是吆喝“白龙江黑龙江统统可以寄”的信纸信封,便是推销“摔伤跌伤打伤刀伤枪伤一样有效”的狗皮膏药。有了这般经风雨见世面的跑码头经历,“老江湖”自是不甘雌伏于F君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的足下,时不时的要进行挑衅一番,力图证明自己也是一条好汉,而且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好汉——当然,只要F君一伸手,“动口”的好汉立即甘拜下风,口中连连念念有词:“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手”……
我很快睡着了。其间,醒过两次。换句话说,也就是头顶上的大灯泡亮了两次,时间不太长,也就那么几分钟的光景,当灯一暗之后,我重又迈入梦乡中去了。
第一次灯亮,是“小浦东”“老无锡”等几个人下来了,他们拧亮了安在防空洞门口的电灯按钮,走下来以后也就各自往空置着的长条凳上一躺,丝毫没有打扰他人睡眠地立即熄灯完事。很识相。
第二回的灯亮就没这么清静了。当开灯的人走进防空洞的时候,“老江湖”第一个发出了声音:“防空洞重地,非熔铸车间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喂,阿凡提,我是在说你呢!”
“阿凡提”是铝箔车间刚进厂的一个学徒工,因经常胡吹乱侃阿凡提的故事而得其名。
“阿凡提”没有开口,F君却搭上了腔:“老江湖,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订立规矩了?可惜呀,我不批准!阿凡提,你愿睡哪儿就睡哪儿去,这是我特批的!”
就在“阿凡提”睡上了长条凳并且同时用一件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棉袄往身上盖的时候,“老江湖“忽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F君啊,你不要好心办坏事:万一阿凡提的车间里有人来找他去做生活,见到上班时间防空洞里睡大觉的这一屋子的罗汉,汇报到厂部去的话,那就有我们的热闹看啰!”
F君的回答简单明了,仅一个音节——伸手“啪”地一声拉熄了电灯开关。
当时,这一屋子睡大觉的罗汉们谁也没有将“老江湖”的话放在心上。事后回想起来,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可真是金口啊,一言九鼎!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灯又亮了。可是,奇怪,久久地不见有人走下防空洞来,第三次被惊醒过来的我知道,这位开灯人一定不是熔铸车间的,一定不熟悉从门口下到地下防空洞的通道,因为这一长溜阶梯的通道里没灯,黑不咕咚地只能扶着墙壁往下行走。
果不其然,好半天才听到脚步声,我从棉袄下探出脑袋一看,嘴里叼根香烟站在面前的,却是铝箔车间的一排长张小海——那时都时兴很革命也很好玩的军事编制,车间主任往往就成了连长,工段长成了排级干部,班组长原地踏步则还是班长。


这张小海或许是第一次踏进防空洞,一见这横七竖八地朝天睡大觉的人,不觉蒙了。张小海到底是块料,在不便于掀起棉袄验明正身的情况下,只得在众多的打鼾声中扁起嗓子细声细气地叫唤了:“阿凡提,阿凡提,做生活了!”
呼噜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棉袄下的大嗓门:“谁在这里装神弄鬼的?滚出去!”
我听得出来,这是“老江湖”的声音。
张小海不为所动,还在喊魂似地紧一声慢一声地叫唤:“阿凡提,阿凡提!”
就在这时,整个事情发生了“突变”!
“啪”地一声,有人把灯关掉了!紧接着便是F君的声音:“揍这个半夜三更装神弄鬼的家伙!”
话音未落,黑暗中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拳头打击声!
我大惊,好一会才醒过神来,连忙从长条凳上翻身坐了起来,大叫道:“开灯!快开灯!”
灯光重又亮了起来。我看到了目瞪口呆一幕:只见好几件破棉袄扔在了张小海的头上,张小海老半天才从破棉袄白花花棉絮的重围中将个大好头颅挣脱出来,嘴上原先潇洒地叼着的香烟也没了影踪!
张小海脸色铁青地朝着四周坐了起来的罗汉们连连道:“好,好,你们动手打人!”
他一眼看到了阿凡提,不觉更是火冒三丈:“阿凡提,你,你等着!”
张小海头也不回地转身奔向了通向出口的通道,不一会从地面上传来了“咚”地一声重重的摔门声。
我摇了摇头:“你们,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张小海让你们这么一闹,他的脸上怎么下得来!”
“老江湖”笑了两声,说,你不要听听声音蛮大,其实一点儿也不会疼,嘎许多棉袄掼在伊身上了,这叫“保护性”击打!
有人在笑。
我不同意,说,这种玩笑开得不合时宜,过火了!
无人搭腔。
在久久的寂静声中,突然地爆出了阿凡提略带哭腔的声音:“我,我怎么办啊……我没办法回铝箔车间了……”
F君站了起来:“走,阿凡提,我陪你一起去找张小海!”
我看了看F君:“你陪他去?你怎么陪他去?”
F君很洒脱地一笑:“你放心好了,我去向张小海赔礼道歉,还不成吗?他又不是厂里什么了不起的红人,‘对不起’三个字还不够重量还压不起他这杆秤?”

上海铝材厂(王绍淼摄影)
那个晚上,不,是那个凌晨,发生在防空洞里的事情就这么简简单单地结束了。后来,当它演绎成一场政治事件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版本应运而生,甚至说防空洞里还有女同胞仰天而卧,男女混居——幸亏事后的调查否定了这一杜撰。有人当时就向车间主任王大民据理力争:熔铸车间的女人从来就不进防空洞的,她们的休息室在楼上的女子更衣室!否则,岂不太黄色了!当然,此人说的也不尽是实情,女人们不进防空洞是在夜班时段,而常日班早班甚至中班时,她们还是有些不守妇道地进入防空洞的。王大民岂能不知道这个半公开的秘密?只是他没有挑明罢了。
记得那天下班时,每个人都因为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而容光焕发,并且在到食堂里去吃早餐时全都胃口大开,汉子们不但人人要了一碗大排面吃了个底朝天,还要了好几片金黄喷香的“吐司”作为“加餐”。熔铸车间的人就是这样能睡能吃!
事发是在十天以后。十天以后的我已经不在厂里,临时借调到公司里写“小评论”去了。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已是万家灯火,才进得家门就听到父亲说,有同事在等你,来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目光已经捕捉到了F君的身影。我几乎不敢相信似地打量了一回F君,数日不见,居然憔悴了许多,往昔一见面就“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乐天派神情仿佛离他远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接下来发生的情景让我大吃了一惊,F君老半天才以我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带了那么一丝哭腔的神态说出了一句话:“我,我已经成了局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主犯!”
我一时回不过神来:“反革命?主犯?你干了些什么?”
F君苦笑着说:“就是那天夜里的防空洞事件……”
我连连摇头:“防空洞?还事件?不可能,绝不可能上纲上线到什么‘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
F君的话将我的全部疑问击碎了:“我,已经被隔离审查一个礼拜了!今天下午才把我暂时放出来……”

管新生1966年大串联在北京天安门
我不知道也根本无法理解,那么简简单单寻寻常常的一次发生在工人中间带有玩笑性质的“打打闹闹”,怎么一下子就乘上了直升飞机长上了翅膀飞到政治事件的云端里去了,这也未免太荒诞了吧?
F君说,在他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几乎天天被押到班组里低头认罪,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而那一个凌晨同在防空洞里仰天而卧的人,全都自愿或被迫地站出来跟他划清界线,向他猛烈开火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老江湖”,“老江湖”坚持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既没听到也没看到更没感觉到任何事情任何动静任何情况,因为他一觉睡到南天门去了。
F君又说,厂革命委员会已经决定在下礼拜四召开“阶级斗争新动向大会”,不但勒令F君上台向全厂两千多号职工读检查——不不,是读“认罪书”,而且区公检法届时还将宣布对他的处理——拘捕……
等一等,等一等!我叫了起来,怎么越听越严重了?这样吧,明天我到厂里去,先找车间主任——对,就是找连长王大民说一说那天凌晨防空洞的事情,说不通的话,我就去找厂里的第一把手……
F君连连摇头,别找了,找谁也不管用的。
我说,干嘛不找?这天下还有没有一个“理”字了?怎么可以这样胡乱给人扣政治帽子……
F君说,你找到天边也没用!你知道是谁给我定性的?
我翻了翻眼睛,说不知道。
是局里第一把手亲笔指示的!他们给我看了那几个蟹爬一样的钢笔字的批示:这是发生在上海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必须予以迎头痛击!
我似乎还有些不信邪,说,局里不了解真实情况,其实……
F君叹了一口气,他们根本不想知道真实情况,你也别瞎搅和,这几天他们就一个劲儿地在追问我的黑后台呢,别到时候把你也扯上!千万别来拾皮夹子!
这句话似乎根本不像是F君能说得上来的。我的心上一凛,这时,只有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F君在被隔离审查的短短几天中思想和灵魂已经经过了怎样的洗礼。
我想到了中世纪宗教盛鼎时期的一个名词:炼狱。
F君接下去说的话几乎要让我这个班组里的秀才也要望尘莫及了。F君说,他听头头们传达了上面的精神,北京出了个“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难道上海就没有?必须要抓个典型出来!
F君苦笑了,也怪我F君背时,不迟不早地撞上枪口去了!对了,你知道防空洞事件发生的日期吗?嘿,你想不到吧,和北京的一模一样,而且丝毫不走样:四月五日!
我微微地有了些诧异,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没搞错?
F君摇了摇头,我哪里记得五日六日的,还不是专案组在这些日子里天天对我吼啊吼的让我长了记性?哦,忘了告诉你,这个专案组是局里指定为我个人特别设立的!王大民?第一把手?他们的级别差老鼻子呢,全部没用,靠一边歇着去吧!真没想到,我从小练体操,也得过不少的奖,可哪一次都比不上这一回,真他妈的出名了,出大名了!
就在这时,母亲来叫吃饭了。
回想起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沉甸甸的一顿饭,才扒拉了不几口,胃口就坏了,吃不下去了。F君倒吃得有滋有味,大口划饭,大口吃菜,大口喝汤,还说这是他最近吃得最为舒服的一顿饭,因为旁边没那些文攻武卫看管着。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就是一个字:爽!
就是在吃饭的当儿,我才明白了F君来找我的真正目的:请我代写检查,或者说是捉刀代笔书写“认罪书”。明天一早就得交专案组。
我在班组里本来就是大家伙儿的“代笔人”,学习《毛选》心得,班组竞赛倡议书,好人好事表扬信,甚至一些纯属个人隐私的情书,都是从我笔底流淌出来的。代写“认罪书”,倒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我斟酌了许久,才说,要写也不难,但有一点,绝不主动给自己扣政治帽子,什么天安门什么反革命什么政治事件,一概不写!不写认罪书,只写检查书,总不能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吧?
F君犹豫着说,这能行吗?
我一笑,什么叫能行什么叫不能行?你以为你的认罪书就一次通过啦?不,起码得让你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大修大改几回,不然过不了这道关!
F君信服地点点头,那就写吧,就这样写!
在喝完一杯绿茶,抽完三支“前门”烟之后,我落笔了。
当一切全都忙活完了之后,已是夜深。
第二天晚上,我与F君又见面了。
F君刚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坐下,便将那份《我的检查书》扔在了我的面前,沮丧万分地说:“没能通过,他们说……”
“他们说,不深刻,不老实,不合格,没有触及思想灵魂,妄图蒙混过关,重写!是不是这样?”
F君愣愣地看着我,说你这一回可真成了诸葛亮了,一字不差,你看!
于是我看到了在《我的检查书》上果真有粗黑的铅笔写道:不深刻,不老实,不合格,没有触及思想灵魂,妄图蒙混过关,重写!
“怎么办?又要、又要请你重写了。”F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
我笑了笑,“没关系,山人自有锦襄妙计!”
在F君惊诧的目光下,我拿出了一叠报告纸,细心地数了五页放在F君的面前,说这是你的第二份检查,尔后又数出五页纸,又说这是你的第三份检查。
F君突然就叫了起来,你,你全都给我写好了?
我笑了一声:事不过三嘛,所以我就一二三地给你全部写好了,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将第一稿的文字重新组合了组合,你回家去誊抄一遍,然后一份一份地交上去,你没事了,我也就没事了。
F君连连点头,谢谢你,你,你连我下辈子的检查都写完了!说着说着忽然又迟疑了起来,万一,万一还是通不过呢?
我笑了,不会不会,你尽管放心好了,这第二份检查书他们一定会批上“仍不深刻,重写”,第三份嘛就只有两个字了:“可以”,这样你就很“可以”地蒙混过关了。
F君听到这儿,不觉笑了起来。
二十四小时之后,F君带到我面前的第二份检查书上果然是六个字:仍不深刻,重写!
F君和我相视而笑。
四十八小时之后,我们忽然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没有 “可以”这两个字,看到的是另外两个字:“重写!”
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低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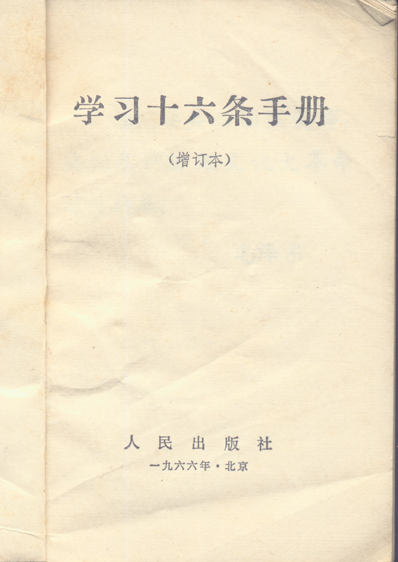
我看看F君又看看《我的检查书》,忽然冷冷地道:我想到了一个高招!我说,其实很简单,把第一份检查书重新誊抄一遍,当作第四份检查书交上去,若再通不过,则以此类推,第二份便成了第五份,第三份则是第六份,如此往复循环地让三份检查书老子生儿子儿子生孙子孙子再生重孙,则能祖祖辈辈生生不息永无止境地繁殖下去……
我还没说完,F君已经让一口茶给噎住了,接着便将茶全数喷了出来,纷纷扬扬的茶水在空中变作了无数细小的水珠儿,尔后溅了我一头一脸,这时F君才将他的话问了出来:这,这行吗?
我抹了一把脸说我还没说完呢,我说现如今的文章本来就是天下一大抄,规定词语规定语境规定格式就这么点,雷同的也就是最时髦的,这一篇和那一篇差之不多,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份检查书的底稿统统没留在对方的手上,真要核对也没法核对,还不是一遍过的事吗!那就索性拉洋片似地一遍遍过罢。
F君呆了老半天才以没把握的口吻说道,那,就试试吧,但愿我们能成功。
第二天晚上,F君来了,只是检查书上这一回的批语是:态度较好,仍需重写!
看着这八个大字,我们全都笑了,“蒙混”原来真的可以“过关”!
第五份《我的检查书》终于盼来了两个大字:可以。
只可惜,真的到了这个份上的时候,我和F君偏偏笑不出来了。
明天,因为明天F君就要被拉到全厂两千多职工的批判大会上去读这一份《我的检查书》了。
这个全厂大会很荣幸地升级了,名称已经由原来“阶级斗争新动向大会”的初级阶段攀上了无限风光的险峰:“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审判大会”。
这个审判大会,我没有参加。
我不敢去。我不忍去。我不愿去。
因为我不敢不忍不愿看到F君这个“反革命”主犯会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管新生1970年代上海铝材厂作炉前工
所以,后来的情况我是听说的。给我说的便是当事人——F君。F君说,大会还没开始,公检法已杀气腾腾地开来了一路鸣响着警笛的三辆警车,并且就停在了会场的大门口。
F君是在一片口号声中被押上主席台的。
F君说,当他面对着突然之间跌入一片宁静中的大会场,将嘴巴凑近了麦克风时,他的灵感驱使他冷丁喊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革命口号:“打倒F君!!!”
整个会场惊愕了一分钟,旋即如同抽风似地爆起了一片参差不齐的呐喊:“打倒……F君……”
F君最为得意的一笔是,他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地以最标准的国语朗读了《我的检查书》,非但一字不错,没有破句地将事实过程清晰的表述了一遍,而且绝对没有把任何政治帽子像扣屎盆子似地往自己的脑袋上扣。
这时候的F君,早已忘记了这是审判大会,在他心目中回响着的只是昨夜他和我定下的基调: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在全厂工人师傅们面前的表演了,那么就把它当作是“我的舞台”!
F君其实还是蛮有表演天赋的。一年半以后,当我陪伴他去参加恢复高考后第一次招生的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考试做小品时,他就是以“我的舞台”的心态投入表演并在十几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复试的。
审判大会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政治大气候的微妙变化,也许是局里第一把手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批示没有得到上头的上头的首肯,也许是F君的《我的检查书》写作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捞不上来一根政治稻草,也许是“也许”的不确定性,反正大会结束之后,F君既没有被拘押,更没有被逮捕,竟然成了一场轰轰烈烈开场草草率率收场的政治闹剧。
当F君莫名其妙地发现身后管押他的两名文攻武卫不见了时,他已莫名其妙地走出了会场。更让他莫名其妙的是,会场大门口的公检法的警车也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我那天没上班。我怀着一种参加追悼会的心情坐在陋室里,像关禁闭似地一整天没说一句话。
当F君突兀地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大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一天,我们第一次一起去喝了酒。第一次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最后,我们是唱着歌踏着满地月亮的影子回家的。
有人说,如烟往事。又有人说,往事并不如烟。
如烟,或不如烟的往事中,终究有沉淀下来的东西,那叫作不灭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