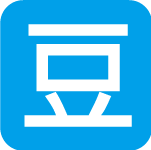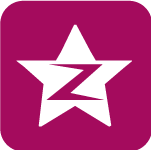用爱与专业技能伴你夕阳从容——记复馨社工师事务所
朱凌1
当己亥猪年春节的脚步临近,各家各户忙着准备过新年的时候,复馨社工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有人在加班。一直忙碌到小年夜,复馨的社工、志愿者们终于给近两千位老人寄出了全部的新年贺卡。新桃换旧符的日子里,老人们已经习惯了复馨的问候与新年一同到来,这是清寒的冬日里,最温暖的惦念,是对一个个在岁月里斑驳沧桑的生命,最贴心的陪伴。
2009年,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杨浦区民政局根据双方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成立的复馨社工师事务所,是国内首家由区校合作推动成立的专业社工机构。
这是2019年初,一个微寒的冬日早晨,距离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不到一个月,街道上,过年的气氛渐浓。五角场街道活动室里,复馨社工师事务所的社工和志愿者们早早地到来,布置好会场,等待前来参加新春联欢会的老人们。这样的新春联欢会,要连着举办十几场,分别在杨浦区的十几个街道举办,来参加活动的老人们,是复馨社工师事务所的服务对象。他们都是杨浦区的优抚对象,有的曾经历峥嵘岁月,在战场上立过功负过伤,有的是烈属,在过往的岁月里,他们比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付出过更多的血和泪,而今,脱下戎装,他们都已是迟暮之年的老者,和这座城市里大多数的老人一样,会为儿女操心,会为病痛发愁,期待着来自外界的关心。

新春联欢会
这是一场新春佳节前的联欢会,也是老人们期盼的大聚会。有些老人到了活动室,就开始忙着换衣服——她们有表演节目的任务。更多的老人则是开心地互相打招呼、聊天。这样的联欢会,每年有两次,一次是春节前,一次是八一建军节的时候。老人们的参与热情很高,有些耄耋之年的老人,平时很少出门,也会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前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见到一些老朋友,可以一大群同龄人凑在一起热闹一下的机会。

八一建军节联欢
时钟指向十点,作为新春联欢会主持人的社工李响走上台,一声甜甜的“爷叔阿姨们,大家新年好”,开启了新春联欢会的大幕。精心排练的歌曲、简单好玩的互动游戏、紧张兴奋的抽奖穿插进行,老人们争相举手答题,兴致所至还会站在观众席里高唱一曲怀旧的红歌,回忆年轻时激情荡漾的峥嵘岁月。
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联欢会在社工和志愿者们集体合唱的《难忘今宵》中结束,不少老人却流连在会场。复馨社工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朱金兰被一群老人围住,热络地聊着家常。
“朱老师是我们的贴心人,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喜欢跟她讲。”
“复馨真的很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让我们感到,社会没有忘记我们。”
复馨社工师事务所已经为这些老人服务了六七年,老人们用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感受。
2
每天,在上班高峰时段过去后,上海的公交车上,一些大卖场的班车上,总会满载着老年人。当年轻人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忙碌,城市的大卖场、小菜场、医院、公园、社区活动中心里,老人们开启了自己一天的活动。
上海是中国老龄化最早的城市,老年人口率全国第一。上海也是中国大陆最早开始发展社会工作机构(社工组织)的城市之一。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工作机构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发展壮大,在面向老年群体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时,社会工作机构承担了许多政府不好做、不便做、做不好、没想到的社会服务,逐渐成长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
依托着复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背景支撑的复馨,在最初在走进社区服务时,也碰过钉子。最初,复馨招募了年轻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作为志愿者,他们都具有良好专业素养,但是,年轻的他们对于老人们的经历和问题不了解,尤其当话题涉及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他们更是无法回应和解答,这使得他们与老人们建立专业关系产生了阻力。
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的政工师朱金兰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加入了复馨的队伍。整整一年时间,朱金兰的工作就是守着一部热线电话,每天接听老人们打来的电话,倾听他们的烦恼,疏导他们的抱怨,为他们解析相关的政策,解答各种疑惑。渐渐的,老人们知道复馨有一个接听热线的朱老师,很懂政策,很热心,都很愿意跟她讲讲自己的心里话。
与此同时,在挖掘社区资源,招募有社会阅历的志愿者的工作也开始启动。志愿者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入户探访,通过入户探访的方式,一方面向服务对象送上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以及社会的关心和尊敬;另一方面要掌握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个别化需求,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和开展跟进服务,争取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使他们在生活中感受更多的自尊和快乐。
招募来的志愿者大多都是社会活动积极的参与者,有些还有过在社区里工作的经验。翁锁珍就是这样一位志愿者。“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有居委会工作的经验,还经常参与公益活动。我觉得自己是可以胜任志愿者的工作的,不过,真的开始做了,才发现光凭以前的这些经验是不够的。”翁锁珍这样告诉笔者。
复馨的专业社工为志愿者们进行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让他们了解到,什么是助人自助,什么是案主自决,如何在沟通中使用倾听、同理、澄清等专业技巧。
复馨的服务对象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会遇到普通老年人在生活中可能碰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需要获得社会的帮助。同时,由于他们不同于普通人的经历和家庭状态——他们本人或是家人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他们有获得政府和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特殊需求。

工作照:接待来访的服务对象
丰富的社会阅历再“装备”上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技巧,志愿者们的入户探访,渐渐顺当了起来。
探访的第一步是走进服务对象的家门。探访初期,很多老人对志愿者的到来是欢迎的,但也有不少人并不欢迎志愿者上门,甚至拒绝接受探访。他们中有些认为,志愿者没有行政资源,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有的认为不需要来自社区的探访。有的隔着门和志愿者说话,或是通过对讲机告诉志愿者“没有事,请回去”;还有的甚至有意屡次爽约,试探志愿者的诚意。
翁锁珍在探访老人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被拒绝的情况。每次她都抱着尊重和理解的态度,一次不行就跑两次、三次,用真心去工作。长白街道的烈属孙先生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将,他因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而名列我国首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刚开始探访这位老人时,翁锁珍接连跑了几次都没进得去门。居委会干部劝翁锁珍说,他家的门可能是走不进的。翁锁珍没有放弃,几天后终于联系到这位老人。他告诉翁锁珍,第二天下午三点在家。第二天,翁锁珍提早到达,在楼下等到三点,准时按响了门铃。老人有点意外:“你那么准时。”进了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挂着老人的父亲的照片。老人和翁锁珍简短地聊了几句,递给她一张名片,告诉她,自己父亲的故事上这个网站可以看到,随后就把翁锁珍送出了门。

志愿者翁锁珍与老人聊家常
回家后,翁锁珍上网详细了解了这位先烈的报导。第二次探访时,一进门,她就向烈士的遗像深深鞠躬,表示敬意,然后询问安葬的地方,随后又和孙先生聊起他父亲生前的事迹。老人听出翁锁珍是用心上网阅读过了,感受到了她的诚挚和尊重,终于接纳了这位探访志愿者。
走进家门只是第一步,要做好服务工作,还需要走进老人们的心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志愿者能打开自己的心门,完全地尊重和接纳每一名服务对象。很多时候,细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叫得出服务对象的姓名,是不是熟悉对方的家庭的基本情况,都会影响志愿者和接受服务的老人建立专业关系。
每次要去探访之前,翁锁珍都会提前查阅要探访的老人的资料,翻阅探访记录,想想这次探访如何开始,要做哪些工作。其实,大多数老人并没有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翁锁珍熟了之后,都把她当成自家人,每次她来,就会拉着她聊家常,说说心里话。有些老人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积了一肚子怨气在心里,翁锁珍也总是很耐心地倾听和疏导情绪。
有一回,翁锁珍去探访控江街道的伤残军人廖建民。廖建民14岁就参加了抗美援朝,转业后在夕钢片厂担任领导岗位。几年前他罹患鼻癌动了手术,很少与外界接触,那段时间,单位没有人来关心,社区也没有人关心,他感到自己几十年来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从来不图名利,转业时为减轻国家负担,还主动要求降薪降级。现在老了,自己似乎被社会忘记了。翁锁珍上门时,廖建民正是窝了一肚子脾气没处发泄,足足对着翁锁珍抱怨了45分钟。那次探访回去后,翁锁珍整理材料发现这天正是廖建民的生日,她马上打了电话过去,祝老人家生日快乐。廖建民的妻子特别感动,说我们自己都忘记了这个日子了。不上门探访的日子里,翁锁珍经常会给廖建民打打电话,鼓励他走出家门,和老战友们多联系,和社区里其他的老人多来往,心情也会开朗一些。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翁锁珍被调去负责五角场的工作,廖建民得知后特别舍不得她,还专门为此找到了复馨社工师事务所负责志愿者工作的朱金兰。廖建民80岁生日的时候,朱金兰和翁锁珍代表复馨送去了生日蛋糕,为老人过生日。老人告诉她们,现在自己经常与老战友们聚会,还会出去旅游。每次老人出门旅游都会给翁锁珍发消息,回上海也会发消息告诉她自己回来了。而翁锁珍每天早晨都会给老人发微信保持联系。

复馨为廖建民老人庆祝80岁生日
3
一个社工师事务所,几名专业社工,一支志愿者队伍的服务半径能有多大?复馨的答案是服务了杨浦区12个街道近两千名服务对象。在复馨这几年的工作里,探索出了社会工作机构挖掘社会资源,用滚雪球的方式,将专业与爱心的雪球越滚越大的工作模式。志愿者的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原本是被服务的对象的身影,61岁的伤残军人时维扬就是这样一位志愿者。
有一年“五一”节前夕,复馨社工师事务所组织在控江路街道组织了“劳动最光荣”主题活动。活动开场前的一幕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和他的老伴由一名男子护送着缓缓进入会场。只见这名男子一边推着轮椅,一边与两位老人亲切地唠着家常。目睹这一幕,很多在场参加活动的老人都不由得感叹:“真是孝顺的儿子!”而一旁有熟悉情况的人连忙解释:“他可不是刘叔叔和孙阿姨的儿子,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优抚对象,还是伤残军人。”
故事还得从这对老人的儿子说起。刘亚东与孙杏英是一对烈属,他们的大儿子刘贵彦是一名优秀的雷达技术员,在1984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场战役中英勇牺牲。年近六旬痛失爱子,夫妇两人悲痛不已。孙阿姨甚至为此哭坏了眼睛。如今,他们一位腿脚不便、一位几近失明,平日互相扶持着生活。当复馨邀请两位老人参加活动时,他们既开心又担心,开心的是感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对烈士的尊敬,对烈属的关怀,担心的是自己行动不便,去活动场所的路在他们看来是如此艰难和漫长。
2014年,在培养志愿者队伍的过程中,摸索出经验的复馨社工师事务所开始尝试发动优抚对象加入志愿者队伍,向自己街道里有困难的优抚对象同伴伸出援手。时维扬听说消息后,二话不说就报了名。了解到刘亚东、孙杏英夫妇的情况后,他便提出了“要求”——“以后这两位老人参加复馨活动的出行我包了”。
为了兑现这一句“我包了”,时维扬做得是如此尽心尽力:只要有相关的优抚活动,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他都会提前来到老人家中,护送他们准时到达会场;活动结束后,再负责把老人安全送回家中。回家路上如果老人在外用餐,他便等候着,待两人吃完后继续护送。时维扬的热心与执着很快感动了其他优抚对象志愿者,一股股暖流在志愿者队伍中流动,大家不时伸出援手与时维扬一起接送老人。

志愿者时维扬与服务对象
时维扬不仅每次活动时惦记着接送两位老人,也常常将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放在心上。一次聊天,孙阿姨说起:“我和刘伯伯感觉人老了,上厕所时手没地方可以扶一下都会感到不方便。”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时维扬当场量下了卫生间的尺寸,回家马上上网查询,但是没有找到孙阿姨要的扶手。他回想起孙阿姨说过“控江医院有一种会升降的扶手蛮好的”,就跑去医院查看,然后在网上逐家搜索。找到扶手后他联系了孙阿姨的女儿,告诉她相关的信息。不久,孙阿姨就用上了扶手。
他还时常到老人家中探望。有一天下午,时维扬上门看望二老,未见孙阿姨。刘伯伯起先说老伴外出了,而后又想起她好像在睡觉。时维扬察觉到孙阿姨平日的习惯并非如此,不安地走进内屋,发现孙阿姨似睡非睡躺在床上,无法说话和动弹,而刘伯伯因坐在客厅,对此毫不知晓。凭着经验以及对阿姨健康情况的了解,时维扬立即呼叫了救护车,并电话联系了他们的子女及时送医。孙阿姨被诊断为房颤引发大面积脑梗,经过手术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桩桩件件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两位老人深受感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句话用来描写时维扬与刘亚东、孙杏英老人间的感情再合适不过。孙阿姨每每想到时维扬,就会对人说,“小时的关心让我们觉得就像儿子从未离开”。孙阿姨还对自己女儿说:“即使你哥哥还活着,我也不敢保证他就能像小时这般贴心。我们的小时比儿子还好!”
4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体,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不相同,脾气性格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复馨用专业的工作方式和真挚的关爱,弥合了各种差异带来的鸿沟。
通过近七年的探索、实践和提炼,复馨社工师事务所形成了一套“三级干预服务模式”。 第一级是“支持性服务级”,针对服务对象群体在自尊和自我价值方面的普遍性需要,提供联络探访、节日慰问、社区联谊、参观游览等常规服务。第二级是“辅导性服务级”,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巧,为面临困境的服务对象或其家庭提供个案辅导,同时借助各种社会支持资源,帮助服务对象恢复和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和社区融入,激发个体自我效能,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级是“专家治疗性服务级”。针对辅导性服务中无法解决的个案,开设个案研讨,并由资深社工师、心理咨询师和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等提供专家个案服务。同时与区民政局优安科形成联动机制,对涉及政策层面的个案开展专案研究,寻找解决方案。

工作照:制作慰问卡
57岁的伤残军人徐伟钢去世已经三年,志愿者的探访却没有随着他的去世画上句号。2019年春节前夕,志愿者王章根又一次去看望了徐伟钢的老母亲和儿子。这样的探望,一年会有两次,一次是春节前,一次是八一建军节前后。
徐伟钢是五级伤残军人,转业到地方后,进入强生出租车公司,因为伤病,长期病假了十多年。2015年9月,徐伟钢感觉背部骨痛难忍,辗转多家医院,都没能查出病因。12月时,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且病灶已经扩散转移。徐伟纲的妻子有长期精神病史,一直在住院,二十几岁的儿子也有智力障碍,生活不能自理,平时同徐伟纲80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徐伟纲确诊肺癌晚期后,他的同胞姐妹左右为难,既担心徐伟纲了解真实病情后失去治疗信心,又担心他因不了解真实病情而导致来不及安排后事。此时,经历了严重的病痛和放疗治疗的徐伟钢,仍然坚称自己“没什么病”,希望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从探访志愿者和徐伟纲的家人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复馨启动了“三级干预”,以政工师朱金兰、社工何一枫和几位志愿者为主,组建了工作小组,由项目督导王承思作为个案督导,复馨社工师事务所总干事刘勇提供专家督导。工作小组主要的任务包括:为徐伟纲提供身心关怀、心理抚慰,帮助他提高生存质量,协助处理未了之事,减少遗憾,争取实现善别等。
生命走向终点的最后几个月里,伤残军人俱乐部的伙伴们,轮流来看望徐伟纲。有些常人觉得不知如何开口的话题,在这些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的老兵眼中只道是平常。王章根回忆说:“我们都是伤残军人 ,互相之间的信任度很高,我们都是有话明说的,身后事不要拖,要安排好。”
医院对病人连续住院的天数有规定,复馨帮助协调资源,让徐伟纲在不同的医院间转院,以便在最后的日子里获得专业的医疗照护。老母亲年事已高,妻子与儿子都有精神疾病,妻子的娘家人又撒手不管,让徐伟纲对身后事的安排颇为纠结,甚至请求将财产交予复馨托管。在朱金兰等的协调下,徐伟纲把家中的房产等做了安排,也对妻子和儿子未来的照护做了安排。“徐伟纲家里的事情最终有了各方都认可的安排,他自己走的时候说,没什么遗憾了。”志愿者王章根这样告诉笔者,“我们以前在伤残军人俱乐部关系都很好,他走了之后,我们这些战友还是会经常去他家看望他的母亲和儿子。”
复馨社工师事务所,就这样不厌其烦地从事着平凡琐碎又神圣的助老工作——用爱心与专业技能伴你夕阳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