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王元化在抗战中
朱大建 翁思再
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清华大学举行了国耻纪念大会。会后,学生们在操场上焚烧日货。当时王芳荃在清华任教
要抗战要救亡
1935年12月9日,北平城里爆发学生运动,六千余名悲愤的大中学生涌上街头,举行抗日请愿游行。学生的口号是:“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挥舞小旗,一边游行一边高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此时任清华和北方交大教授,正好在家里休息,他就对王元化的两个正在燕京大学读书、刚回家休假的姐姐王元霁王元美说:“你们的同学,为了祖国的存亡,都在冰天雪地里呼吁,你们怎么能在家里呢,你们要回到队伍里去!” 王芳荃喊了一辆汽车,将元霁元美送到西直门外的游行的队伍中去。事后,当王芳荃任职的学校当局请教授讨论如何处置学生游行之事时,王芳荃首先站立起来发言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良心告诉我,我不能反对学生运动。”
父亲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爱国行动感染了王元化,那年他才15岁,正在育英中学读书。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市民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时,王元化跑到学生临时组织起来的非常自治会,要求参加非常自治会的活动,投入抗日洪流。他被推荐为校刊《课外选课专页》的主编,平生第一次编著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谈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一篇是谈日货走私,虽然只是报纸文章的综合,却也显示他分析社会观察社会的眼光。也正是这两篇文章的影响,引起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学生的注意,捕风捉影地怀疑他和共产党有联系,到校长面前去告状,王元化被撤职了。
然而,憧憬着社会公平公正和民主自由的热血青年的人生理想,岂能被几个特务的威胁吓倒?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同当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一样,正是因为日军的野蛮侵略,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抵抗,使王元化一步一步走向共产党。1936年,在国难当头时,王元化与李克(查先进)、夏淳(查恒禄)一起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开始抵抗日军的进攻,因中国军队准备不足加上装备落后,一个月时间里连吃败仗,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阵亡。守城的29军军长宋哲元率领部队一直抵抗到8月初,只能撤退。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就在日本军队进城那天凌晨一点钟,王元化随父母离开北平南下逃亡。
天下着细雨,古城静悄悄的,街上没有行人。正在病中的王元化,被扶上马车。一家人恋恋不舍地望着街道,倍感凄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青年王元化满腔悲愤。
到了火车站,但见一片嘈杂。这是最后一班列车。许多不愿眼睁睁看着北平城沦陷,不愿在日寇铁蹄下当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平民,这时都在逃难。日寇痛恨知识分子,见到读书人就抓。为了安全,逃难人群中的知识人,上衣不插钢笔,口袋不放片纸,有的还把眼镜也摘下来了。不过王元化还是瞒着家人,把一幅自绘的鲁迅像,两本鲁迅编辑瞿秋白翻译的文艺理论著作《海上述林》,偷偷装入随身的小箱里。家里的藏书,装进一口大缸,心想等抗日胜利后再来取,哪里想到抗战竟如此艰难漫长,一直打了8年才胜利。

《海上述林》书影

火车站人声鼎沸,一片嘈杂
京津路上,迎面不断有呼啸的日本运兵车开过,逃难平民所乘列车时时停下来。仅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它竟整整走了一天。当时天津已被日军占领,出站时,只见日军在站台上杀气腾腾,荷枪实弹。逃难人群走出车站,必须从两排端着刺刀的日军夹道里通过,日军后面还有一些便衣特务,站在高处,凶狠地检查人群,只要看着谁像军人和知识分子,就拉出去架走。王元化一家人就夹在人群中,经过敌人的检查走出天津车站。这种屈辱、恐惧、惊慌、愤怒,加上哀伤的情感,让王元化铭刻心间,那种伤心欲绝的痛楚,永远难忘。
到天津后,由于战事正紧,火车已经无法开行,南下逃亡只能坐船从海上走。那时船运主要靠洋商,从塘沽口出海。王元化的父亲只能在天津租界租房暂居,整整花了一个月,才买到去青岛的船票。在轮船上,王元化在愤怒和哀伤的情绪中,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南行记》,写的正是平津沦陷后一艘开向上海轮船上的流亡人群的生活,后来发表在上海学联主办的特刊《上海一日》上。
出渤海湾到了青岛,刚安顿下来,却发现这里也不是安身之地。原来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已经逼近胶东。于是赶紧再侯船,继续南下。如此辗转折腾,直到十月份才到达上海,此时“八一三”抗战烽火已经熊熊燃烧到最后阶段。
素不相识的热血青年学生来接站,他们手里摇着小旗子,不停地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望着“热烈欢迎平津流亡同学”的横幅,青年王元化和她的姐姐们不约而同,“哇”地一声哭出声来。王元化来到静安寺赫德路(今常德路)金城别墅,找到“平津流亡同学会”总部,他们专门为那些人生地不熟的南下学生提供帮助,解决各种初来乍到时的困难问题。王元化通过这个同学会,联络到了自己的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排演抗日话剧
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妄图迂回包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怕腹背受敌,后撤之路被截断,仓皇撤出上海,八•一三抗战结束。日军占领了上海的中国地界,租界沦为“孤岛”。王元化热情投入抗日活动。他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中恢复了“民先”组织身份,不久考入大夏大学经济系。日寇的侵略使他难以安心经济学,于是开始拿起战斗的笔。1938年写出文艺作品《雨夜》,刊登在文汇报副刊“文会”上,而后便一发不可收。他主要写文艺理论文章,兼顾文艺创作。1938年初,还不到18岁的王元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初,十七岁的王元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
地下党派他去联系学生运动,具体是抓排演抗日话剧工作。王元化通过同学汪玉岑的关系,使汪家在长乐路陕西路口的一所花园洋房,成为“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基地,王元化还代表平津流亡同学会参加“学联”,出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
“孤岛”时期,上海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职业界、学生界,各行各业如邮局、铁路、银行、钱庄甚至巡捕房里的中国人,都组织起救亡团体,他们的一个重要活动方式,就是通过群众文艺演出宣传抗日,鼓舞人民士气。当时上海有200多个业余剧社。王元化负责话剧排演活动的组织工作,于是长乐路的“汪家花园”就成为排戏场所。王元化身边聚集着一批业余话剧精英,经常派他们到各剧社去辅导,帮业余演员化装,兼当导演。王元化本人也常去剧社说戏,有一次他到暨南附中为学生剧团分析丁玲的剧本《重逢》,剧团成员听得津津有味,便说“你讲得头头是道,干脆直接导演算了!”然而毕竟隔行如隔山,业余演员往往需要手把手地教戏,这就难为王元化了,排了两天,败下阵来,只好另请高明。
孤岛抗战文艺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后,地下党就租下一个剧场,逢周日演出,名为“星期小剧场”,地点在今天的新光电影院,吸收团体会员加盟,为群众救亡话剧演出提供舞台。“星期小剧场”很快成为文艺青年向往的地方,王元化在此基础上组建“戏剧交谊社”,进一步把上海200多个剧社团结在地下党周围,上演了60部左右的话剧,涌现出四大导演费穆、黄佐临、吴仞之、朱端钧;四小导演吴天、胡导、洪谟、吴琛。
后来成为王元化妻子的张可,是“星期小剧场”演抗日话剧的活跃分子,王元化和张可也就在这抗日舞台上,自然地、悄悄地绽出爱情的新芽。王元化认识张可的时候,张可正在暨南大学外语系读英国文学。年轻的张可,身穿淡蓝竹布袍子,简单又素净,气质高雅。王元化在组织剧社活动时,读了张可发表的一些散文,心生爱慕,常常与张可谈艺说文,相知日深,感情愈深。
历艰险皖南行

1938年,王元化初到上海时的留影
1939年初,受地下党组织派遣,王元化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组团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王元化参与筹集书报、药品等慰问品。一些进步文艺青年,将随团赴皖参加新四军,加起来有30多人。行前,才16、17岁的白沉被他的两个姐姐送到王元化面前,这是一位在“星期小剧场”展露才能的小伙子,他姐姐说:“弟弟年轻幼稚,烦您把他带到皖南,交给革命,一路上拜托您多关照”。其实,王元化不过才比白沉大两岁而已,在自己父母眼里,何尝不是个孩子?不过,当时慰问团里党员极少,王元化又有少年老成之相,自然成为重要骨干,谁也不会小看他。慰问团要出发了,王元化的母亲看到儿子冒险远行,难过得哭了起来,知子莫如父,父亲王芳荃毅然对妻子说:“他向往革命,让他去吧。”
为安全起见,30多人的慰问团分几路赴皖南。慰问团团长是吴大琨、副团长是杨帆。王元化凌晨乘飞康轮从十六铺起锚开船,刚刚朦胧入睡,哪知轮船出了吴淞口就被敌人汽艇截住,日寇上船搜查,四处寻找抗日书报,将旅客全部赶到甲板上,一个个盘问,看看头上有没有帽印,食指上有没有老茧,这是在搜捕中国军人。王元化和散在各舱的团员沉着应对,但随慰问团到第三战区去的四位军人伤病员却被日本兵抓走了。第二天,上海报纸刊登“今晨日军飞康轮抓走四个抗日分子”的消息,王元化的母亲以为儿子可能在其中,难过得大哭一场。后来接到王元化从温州寄来的家信,母亲才稍稍安心。王元化等从温州乘民船溯瓯江而上,借道青田,来到金华。这里是第三战区的中心,长官是顾祝同和上官云湘。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王元化在这里见到了邵荃麟、骆耕漠等我党文化精英。慰问团里准备投奔第三战区所属新四军的演剧人才,就在这里先演了几个节目。此时,适逢周恩来从皖南视察后来到第三战区,王元化在一个小旅馆里见到他。同时在国共两党担任要职的周恩来,穿着缴获来的黄颜色日本军大衣,亲切地问:“上海的情况怎么样?”王元化挤在人群中汇报了各界救亡工作,重点谈了抗日宣传,他才19岁,居然毫不怯场,侃侃而谈。其实当时国民党已经在内部下达了“禁制异党活动”的命令,周恩来告诉面前这位青年人,自己作为国民党总政治部副主任,来到这里居然也有特务监视,宪兵来这里声言说要检查周恩来,被周恩来严词骂了出去。由于周恩来的来到,金华还遭到日军的空袭。
在金华盘桓期间,王元化病倒了,高烧热度很高,幸亏由他带去投奔新四军的青年郑大方日夜照料,下挂面,炖鸡蛋,终于使病情渐渐好转。郑大方在上海时受到王元化的影响,他俩一块儿研读过日本人藏原惟人写的辩证唯物论。
离开金华后,王元化离开慰问团大部队,率慰问团中去新四军的小分队沿青弋江步行,第一天走了80里山路,王元化脚上起了三个大泡。山道一面是绝壁,一面是悬崖,有时遭遇对面有人骑马而来,王元化只好身靠绝壁、背贴马肚,先让他们通过。
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慰问团小分队来到小旅舍住宿。那里地上积水,只能是两个人合睡一块窄窄的床板。慰问团里唯有一名女青年,她姓汪,提出和自己合睡对象是王元化。是夜,这两位抗日青年,一男一女,和衣而卧于窄板床,毫无杂念。晚年王元化回忆说,当时的进步青年,心灵就是这样纯洁。
就这样辗转到达皖南,顺利送上药品、书报和青年才俊,还赠给新四军一面锦旗,上写“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王元化从未使用过的牙膏管内取出由领导亲笔写的介绍信。负责与王元化联络的是原在上海写理论文章的冯定(解放后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他的笔名叫贝叶,有着“贝叶传经”的意思,意为用文字传播马克思主义。冯定非常热情地接待王元化。冯定穿一身灰布军装,右臂上缝着一块新四军的徽号,上面印着“抗敌”两个字,字下面还有一个端着刺刀冲锋的军人木刻像。冯定个子不高,身材瘦小,剃着光头,戴着眼镜,脸上皱纹很多,说话声音不高,但精力充沛,一直是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的样子,情绪高昂。冯定告诉王元化,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要接见。于是王元化跟着冯定,来到袁国平的办公室门外。冯定喊一声:“报告!”袁国平在里面说“进来!”进门后冯定“啪”地立正,打一个敬礼,介绍说:“这是上海地下党派来的白蚀(王元化的化名)同志”。军队里的礼节,使王元化感到十分新鲜。那天谈话后,袁国平还挽留他共进午餐。王元化应邀在新四军教导团、服务团作关于上海救亡运动情况的报告,全文被整理发表在新四军《抗敌报》上。王元化还在那里多次看新四军服务团的演出,看过张茜(当时尚未与陈毅结婚)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中演的小白菜,看过吴强(后来当了作家写出长篇小说《红日》)演的阿Q。王元化初步体验了革命军旅的生活,并同那里的文艺工作者接触,知晓了新四军中文化人的文艺思想。
在新四军军部服务团,王元化被安排在辛劳住的单独的院落里。王元化很高兴,他遇到故人,晚上可以畅谈了。
辛劳是年轻的进步作家,1938年春天,王元化带着地下党的介绍信去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家难民收容所去见辛劳,当时辛劳在难民收容所做难民的文教工作。王元化想请辛劳去“平津同学会”谈谈文学创作。王元化说明来意后,辛劳用一双湿漉漉的鹰眼注视着王元化,好像要在王元化身上搜索出什么可疑的东西。王元化发现,辛劳长着一张狭长的脸,一头蓬乱的卷发,穿着一件乌克兰衫式样的农民服上衣,身上有一种浪漫的气息,一下就感觉到辛劳在模仿普希金。王元化对辛劳的第一个印象并不好。辛劳谢绝了演讲的邀请,但写了一张便条改请别人去讲。以后,王元化对辛劳的散文和诗发生了兴趣,由兴趣再到喜爱。1938年下半年,辛劳带着难民收容所一批青年难民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在新四军军部的院落里的遇到辛劳,王元化多高兴啊。这个院落,辛劳住一间,聂绀弩住一间。王元化去的时候,聂绀弩正好去金华了。不料,到了晚上,王元化和辛劳谈文艺问题,竟激烈争论起来,双方都动了感情,拉长脸谁也不理谁。一夜过去后,两人又重归于好,乌云散尽。当时的文艺青年,就是那样的单纯明朗天真。辛劳将他写的长诗《捧血者》给王元化看,辛劳还为王元化朗诵,朗诵时,辛劳的脸因兴奋而发红,眼里闪着热烈的光,嘴唇在颤抖,声音也在颤抖。王元化被辛劳的诗所感染,也领会到辛劳诗中的美和真情。后来,辛劳在抗战快要胜利时,经过专门与新四军作对的顽军韩德勤驻地时,被抓住关进监狱死于狱中。王元化晚年时,写了《记辛劳》散文,深深地怀念这位性格独特的诗人。
从皖南回来后,王元化多次在进步青年中作报告,介绍新四军见闻,并创作报告文学《出征》。他根据在皖南搜集到的材料,发表了长篇论文《艺术-宣传-宣传戏剧》,其中“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提法,为上海文坛所首见,带来一股清新气息。和王元化一起到皖南的三十多个知识青年中,很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优秀人才。白沉成为电影军事片导演。郑大方参军后,作战勇敢,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一门大炮,立了大功。后来当营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办好“文艺通讯”
敌伪统治凶残暴戾,但在党的地下文委领导下,抗日的进步文化活动就像炽热的岩浆,在地底下秘密地流动。当时,隶属江苏省委的地下文委,第一任书记是孙冶方,副书记是顾准。文委下设若干小组,文学组由戴平万、林淡秋各任一个组的组长,小组成员有钟望阳、林珏、蒋锡金、蒋天佐、束纫秋、肖岱、王元化等。自皖南回来后王元化从戏剧组转到文学组工作。这个时期,王元化发表过小说、散文、杂文等,用的笔名除佐思外,还有洛蚀文、方典、函雨等。1939年他在《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鲁迅逝世纪念特辑》中发表长篇论文《鲁迅与尼采》,1940年在《戏剧与文学》上发表长篇论文《现实主义论》,显示出他在文艺批评、治学方面的才华。在地下文委的领导下,王元化和梅雨、林淡秋等人共同组织和主持文艺通讯工作,开拓群众抗日文化活动新方式。 王元化一直记得顾准第一次来文艺通讯支部开会的情景。顾准又潇洒又和蔼,拎了四大包水果、点心(顾准是潘序伦会记事务所高级职员,薪水高,又有会记著作版税),和文艺通讯支部同志开会时一起吃,他富有人情味的、轻松活泼的工作作风,很受文化人党员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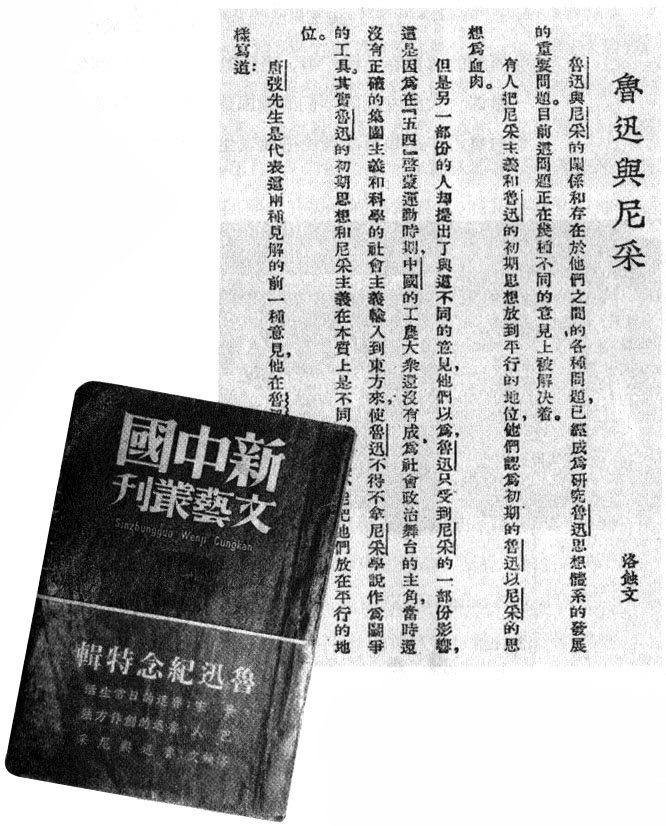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王元化在《新中国文艺丛刊》以笔名发表的长篇论文《鲁迅与尼采》
文艺通讯工作简称“文通”,是上海地下文委在抗战期间,开展群众抗日文化活动的另一种方式。文学组搞“上海一日”的征文活动,请青年文学爱好者写上海救亡活动中的真人真事,在地下党控制或联系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从中发展通讯员,并由他们进一步团结其他青年。王元化到“文通”后负责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则由钟望阳负责。他们办的公开刊物起先叫《野火》,后改为《春风》,编辑部承担辅导作者的任务。表面上,“文通”类似现在报纸、刊物的固定作者、通讯员制度,实际上它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通过王元化一段时间的工作,建立起“文通”总站——分站——支站,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网络,可以逐层传达上级指示、文件精神。 “文通”的日常学习分作政治和业务两类,前者主要是不断地作形势报告,演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局,介绍抗日前线的战况,分析抗战的前途,这是大家所特别关心的。业务学习就是写作辅导,当时往往选用苏联的教材,如苏联作协《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以及高尔基辅导“工农通讯员”的文章等。王元化也专门写过“文通”辅导报告,题为《关于文艺通讯》,论述了“文艺通讯的意义”、“怎样做一个文艺通讯员”、“怎样写文艺通讯”等问题,油印后下发供学习,后来分三次在华美晨报副刊连载。
通讯员入选的文章,除了登载在《野火》《春风》外,王元化等还推荐发表到其它报刊,如文汇报、大美晚报、华美晨报、神州日报等。在此过程中,“文通”队伍如滚雪球似地壮大起来,后来达到二三百人。这些人后来多数参加革命,而且成为骨干,解放后成为我党的干部。还有些“文通”成员干脆投笔从戎,由地下党陆续送到皖南,或其它抗战前线(如锺敬文、田青)。有些人(如何为)则一直在文坛辛勤耕耘。
由于形势变化,文艺通讯支部被顾准撤销并入其他支部,王元化不了解这是为了适应日军可能南进的形势变化,写了一份长达6、7页纸的报告表示反对,王元化的意见并不正确,顾准却毫不责怪,反而说,王元化敢于向领导提出不同意见,精神可嘉,是个人才!当时的党内上下级关系,就是这么健康单纯!为了给顾准写秘密报告,王元化还为顾准起了个化名“王开道牧师”。不久,顾准、孙冶方先后奔赴苏南抗日根据地,又去华中根据地。
分管《奔流》杂志
1941年春,上海地下党文艺总支由黄明任书记。那时,党组织正确地估计到日寇将会南进和英美交战,租界可能会沦陷,上海局势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为此,地下党将比较暴露的王任叔、林淡秋等党员作家撤退至华中根据地,由比较隐蔽的王元化、肖岱和新来的总支书记黄明组成负责文艺工作的党组织。王元化分管《奔流》文艺丛刊,并联系文学组方面的党员以及党外人士。该刊后来改名为《奔流新集》,参加编辑的有楼适夷、满涛、锡金。满涛是张可的胞兄,是翻译家,《奔流》编辑部设在满涛家里,实际上也就在张可家里。1941年7、8月,上海地下党成立文艺工作委员会,黄明任书记,王元化、吴小佩为委员,王元化负责联系原来的文艺总支。
《奔流》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一方面揭发日寇的暴虐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阴谋,一方面继续坚持现实主义原则,扩大我党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并对文艺界出现过的反动逆流进行斗争。发表过作品如:林淡秋的《渣》《寒村一宿》,钟望阳的《丧事》,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揭露国民党的腐败;越薪即束纫秋的《李德才的遭遇》,控诉日军的暴行。有一批作品是颂扬革命领袖和革命阵营里的作家的,如景宋即许广平的《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莫洛的《陈毅将军》、楼适夷的《怀雪峰》等。发表过的理论和评论文章有:茅盾的《谈技巧、生活、思想及其他》,以及“每月读书”栏里一些作者对名著如《静静的顿河》《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的评价。在《奔流》的撰稿人中,有蒋天佐、戴平万、辛劳、林珏、赵不扬、孙石灵、孙家晋、辛未艾(包文棣)以及仇山(唐弢)、柯灵、朱维基、姜椿芳、田青等。该刊改名为《奔流新集》后,参加编辑的还有楼适夷、满涛、蒋锡金、蒋天佐等。
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帮腔文人标榜所谓“抗建文学”,敌伪方面则叫嚷所谓“和平文学”。“抗建文学”派认为,揭露国民党阴暗面的暴露文学,是帮助敌人破坏抗战,损害了民族的健康,是“病态文学”。为此王元化以“佐思”的笔名,在《奔流》第五期上,发表《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予以反驳,指出暴露国民党的黑暗面,打击少数顽固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这样做非但不损害民族健康,反而有利于医治民族弊端,恢复民族健康。王元化批评某些“帮腔文人”,只反对所谓暴露文学,却把敌伪的“渣滓文学”轻轻放过,忠告他们不要滑的敌人方面去,希望他们不要在既反对“渣滓文学”又反对所谓“病态文学”之间,老是矛盾下去,而应走到进步方面来。此文一出,立即遭到围攻,“帮腔文人”漫骂王元化是什么“卑劣的文士”“黑暗中的蠕虫”。指责作者所肯定的作品,是什么弯弯曲曲忸怩作态的不良倾向。王元化随即发表应战文章《论隐蔽,弯弯曲曲、直接地戳刺》指出,今天“颂扬”鲁迅直接戳刺的人,过去在鲁迅活着时,也曾指责鲁迅弯弯曲曲;弯弯曲曲不是判定作品好坏的标准,正是恶劣环境下顽强生长的表现;标准应该是:是否反映现实,揭示真理,而指责别人弯弯曲曲的人,正是在弯弯曲曲地替抗战阵营内专门吃磨擦饭,发国难财,反对民主,实行倒退的顽固派进行掩饰。
地下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切都在隐蔽中进行。当时文艺总支的定期组织生活,没有固定地方,有时在党员供职单位的办公室,如银行、钱庄等,有时在公园里。如今的静安公园当时是外国人的坟地,里面很安静,居然也一度成为“游击式”地下党过组织生活的场所。那时已是1941年,处于“孤岛”末期,许多同志已在党组织安排下撤至抗日根据地。为了维持刊物生存,王元化和其他编辑们便自愿捐款,虽然大家钱都不多,却还是你十元,他五元,集腋成裘,而且义务劳作,不要稿酬,硬把《奔流》坚持办下去。那个时候,时局非常黑暗,城里常常封锁、戒严,铁丝网将上海分割得像一座座监狱,晚上常常停电,连空气中焕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肃杀的味道。只要楼梯上一传来咚咚的大皮靴声,王元化母亲的心就抽紧了,她以为是日本人来抓她的儿子。日军还到处搜刮军粮,于是上海粮食奇缺,老百姓能吃到碎米、杂粮已是万幸,更多的人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忍饥挨饿是常事。在这样艰苦的局势下,王元化等人还是节衣缩食地在坚持办好《奔流》杂志,这是上海孤岛时期最后一个公开的进步刊物,多么顽强啊。

抗日活动转入地下,王元化充分尝到了在敌人刺刀下丧失家园的痛苦滋味
根据党提出团结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要求,王元化在1941年11月出版的《奔流新集》之二《横眉》上,发表《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一文,肯定张恨水、包天笑等的成就,指出张恨水的文学作品,目的在创造人生、叙述人生,张恨水在“一•二八”后写的《弯弓集》,是充满民族解放思想的。王元化同时赞扬包天笑的《无婴之村》,是“警戒”那些侵略者、好战分子的。包天笑在《小说家的审判》中,以判官阎王作比喻,无情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如用酷刑一般地残酷镇压左翼作家。王元化这篇文章为团结鸳鸯蝴蝶派发挥很好作用。包天笑晚年在香港写的《钏影楼回忆录》中说:“孤岛时期,有一位名叫佐思的青年作家经常上门,他很能说话,是左翼阵营里的人,我的一篇长篇小说《海市》就是应他的邀约而创作的,并由他拿去发表在一份新办的《万人小说》月刊上。”这里的“佐思”就是王元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上海完全沦入日寇之手。这时,上海地下党的抗日斗争,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此,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地下斗争方针,指出在上海沦陷后仍要贯彻周恩来在抗战前就提出的白区地下工作要“勤业”“勤学”“交朋友”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勤业”是指党员要在职业上显出自己的正直和才能,“勤学”是指学生党员要做一个公认的好学生,“交朋友”是指在“勤业”“勤学”的基础上,用多种形式,在敌人的心脏里开展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王元化后来在《我认识的纫秋》一文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我们充分尝到在敌人刺刀下丧失家国之苦。”
坚持独立思考
抗战期间,王元化一边从事地下文委抗战文化的领导工作,一边埋头笔耕,文思泉涌。然而那时他毕竟刚20岁出头,反应灵敏的负面,就是“跟风”。那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通过日本转译过来的,还有些是演绎之作,文艺理论更是照搬苏联那一套,王元化受此影响,文章里难免有机械论和极左的东西。比如上述皖南回来后所写的论文,有些提法就是受了藏原帷人的影响。苏联“拉普派”关于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二元论”理论,最早也是由这位日本左派理论家引进中国的。普列汉诺夫说,艺术作品中有社会等价物,这就把商品两重性的性质引入艺术领域。王元化受其影响,附和社会标准、艺术标准的提法,并以社会标准为第一,写进文章发表出去了。颇有见识的文委有关领导对王元化的观点不以为然,戴平万、林淡秋都希望他能从机械论里跳出来,更不要过多引用那些教条的文字。可是王元化年少气盛,而且见报多了知名度高了,正在沾沾自喜呢,耳朵里听不进批评,有一次戴平万向他正面提出这类意见时,竟被他顶了回去。王元化我行我素,继续以老腔调撰文投稿,于是戴平万、林淡秋就不发表他的文章了。屡投屡不中,迫使他带着困惑去苦读,系统地研读,改进文风。如此约两年时间,他的理论素养得到有效的提高,终于醒悟了,发现并承认了自己过去的机械论问题。这时候,朋友们再见到他的文章时,都刮目相看,说他“脱胎换骨”了。
在思想方法转换的进程中,王元化跨入了1942年。从延安来的文件中,他发现“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论点,这时他有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心里存有疑义,觉得应该商榷。
1941年至1943年,这是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时期,也是上海沦陷后地下斗争最艰难的时期。地下党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撤往华中根据地,原属各委独立开展工作,通过交通员同根据地上级联系。在这个时期,王元化一度担任地下文委的代理书记。他后来向上级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不同意见。这时许多地下党干部随省委领导撤退至抗日根据地,比较能理解他的干部也转换了岗位,王元化的顶头上司刚从延安调来,刚经过“三整三查”,警惕性异常高,自然对王元化所提出的问题很警觉。然而其政治敏感性高得越过了界限,于是乎,学术问题仿佛成了“政治问题”,王元化在文委里开始变得“不可靠”起来。渐渐地,一些会议不让他出席,一些工作不让他做,甚至还让党员 “背靠背”地揭发他言行。
王元化在党内的遭遇是戏剧性的,他21岁就担任地下文委的委员,23岁负责文委工作,可是很快又如火箭般地下来,而且领导长期不安排他工作。对此,王元化并不后悔,并把这种反思精神一以贯之,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人生晚年。他曾说过,正因为自己当年搞过极左,对危害文艺工作的机械论、教条主义有切肤之痛,因此反省起来尤其深刻。
从那时一直到抗战结束,王元化的公开身份是储能中学教师。他化名王少华,每天骑自行车到那里上班,给学生上语文课。他不用日本人编的教科书,而是自编讲义和教材,选讲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文天祥的《指南录》等文章。他给同学们讲鲁迅,讲雨果、果戈里、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在这漫漫长夜中点起一盏心灵之灯,启发这些懵懂孩子们的慧心、悟性和爱国热情。

王元化在上海储能中学教过的学生吴长生、王烈光、黄菊芬等
上课了,王元化走上讲台,翻开书:“同学们,今天讲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王元化把鲁迅收入《野草》的这篇杂文,作为教学生辨别大是大非的首选教材,他要让同学们认识到生活中有些什么样子的“聪明人”“奴才” “傻子”。王元化生动的讲课,大大激发起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欲望,也引起他们对鲁迅文章的兴趣。那几年储能中学先后有50名学生投笔从戎,分赴苏北、浙东、苏南、淮南抗日根据地,其中有20人出自王元化担任班主任的初三班。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这时王元化只有25岁。一个当年由看不惯人间不平、一心抗日而走向共产党的少年,此刻终于尝到了斗争带来的幸福感。
八年抗日战争,八年秘密战斗,意味着两千九百多个日夜躯体与精神的煎熬,民族自尊的隐忍!在这个过程中,他周围也有人掉队,有人颓唐。回首往事,王元化想,如果自己的内心没有对真诚、对正义、对人生的坚定信仰,他的精神或许支撑不到这一天。这几年,家境也变得很清贫,他教书赚来的钱,仅够一天两餐之用。在如此拮据的境况下,他连买一包花生吃,都成为是一种奢望。可是,在等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他怀着孩子般的兴奋,上街买了一副久违的大饼油条,吃得比任何时候都有滋有味。
此时,王元化已不在地下文委的领导岗位。他照例骑着自行车,每天到储能中学上班,去给那些可爱的少年们上课。他不久便到《时代日报》上班,与满涛合编《热风》周刊。他那颗炽热的心,仍然紧贴着祖国和人民;他的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独立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求。













